电影的空洞——一篇关于侯麦电影的学习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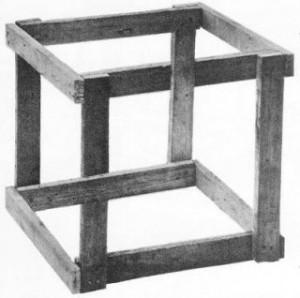 文:田博
文:田博
0、
这是一篇关于侯麦(Eric Rohmer)电影的学习心得,也许写着写着有些跑题,更多的在表达我对电影叙事的看法。因为我一直处在对于电影叙事的失落之中。“轻松”的电影感官们,让我飘飘然进入一时梦境之后,反而得到一种更深的恐慌。“深刻”的电影主题们,让我觉得不堪重负,也觉得滑稽。两个小时的叙事时间,顶多能容纳3、4个意义的转弯。难道电影就只能发挥感官刺激的特长,天生就不是一个合适的思想容器吗?我想说的是,侯麦电影里发现的闪光点(应该说是一些电影叙事的共通点),让我保持了对叙事的信心。比起牛逼哄哄的导演们“轻松的姿态”和“思想的深刻”这些可以伪装的东西来说,叙事的技巧更让我信赖和欣赏,以及这种用技巧达成的最感性的重击。
1、
叙事的首要问题,是容器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形式的边界在哪里?
诗人的选择余地只有几行字,电影导演则拥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自由度更大了些,其实不见得更容易。
如何把大千世界装进一个小核桃里,这是每一个时间艺术家不断向自己发问的问题。
选择自然主义还是戏剧性?选择巴尔扎克还是乔伊斯?这中间的度,构成了每个叙事艺术家与众不同的特质。
一个电影故事,不仅要在理性上把握生活的精髓,还要在感性上赋予银幕鲜活的形象。然而这两者,往往相互对立、相互制约。正如巴赞所说:“叙事的真实性是与感性的真实性针锋相对的。”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编剧的敌人是美术,导演则是要把两者统一起来。
其实,单是在剧本阶段或置景阶段,编剧和美术自身也会面临理性与感性、主题与形象、戏剧性与自然态的敌对。
我先谈侯麦的编剧。
2、
叙事的终极目的,我认同巴赞的表述——“最终为了使生活在电影这面明镜中看上去象一首诗。”
为了达到诗性,必须破坏自然态的平均和乏味,又需提防戏剧性的过度和封闭。
侯麦电影的叙事技巧主要有三个重要手段:
在框架设置上的空洞;
在时间板块中的削平剁小;
在叙述逻辑里的自我反对。
3、
在框架设置上的空洞。
不管是否承认,一个姿态再低的创作者,面对“人物”所代表的“人群”,也是有伦理高度的:他们试图向我们提出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意义。为了试图把握生活这条曲线的轨迹,创作者在叙事的坐标轴上打上几个点,以感觉的笔触连接起来,使别人既看出它的来由、欣赏它的起伏、又能看出它的走向。但是,我们不必天真地以为,那几个点和线就代表生活。要命的是臆想的人,聊臆想的意义,以臆想的线条,抚摸臆想的人生,画者、笔和纸都是这线中的一点。
平庸的电影这样处理曲线:每一场的场任务都说明一个明确的小道理,很多场小道理连接起来,说明一个安全、确切、平庸和乏味的大道理。
聪明的叙事电影,曲线编织的却是“空洞”。
这个“空洞”,不是“言之无物”,也不是老庄的“无”——而是由多个相互矛盾的意义交叉形成的多指向性,是由多种戏剧情境交融形成的强大磁场。有如物理学假设的黑洞,它的引力太强,我们的心灵一旦投入注视,目光便深深掉落其中,不可自拔。
这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失落和最大限度的清醒。
侯麦的《绿光》,迎风而泣的德尔菲娜,游走四方,周围的人单纯地把她的悲戚视为失恋,不断地给她讲述生活该怎么着怎么着。那每一个不同的道理,看起来都足以说服我们活下去,但是德尔菲娜却无法轻信,固执地寻找着她生命中的绿光。
在我看来,叙事的目的就是要捕捉生活的这个巨大空洞。
这个空洞是悲剧的灵魂,是诗意飞出来的地方。没有中心思想,只有中心“空洞”。在这个“空洞”的周围,布满了意义,那些我们因为生活的欲望和怯懦而敷衍出来的种种意义。我们不自觉的围绕着这个深不可测的黑井跳舞,井口的周围布满了血迹;聪明的观众,享受井水的幻想和岸上的安全;少数人则受到诱惑,变身前往井底取水的矿工,虽然事后倍感水的苦涩。
剧作的结构过程如同搭积木。积木就是生活材料。好的故事并不是欣赏积木本身,而是欣赏积木搭建出来的罅隙。就像,诗不存在于词句本身,而是存在于词句的空白之中。
举个例子,聂鲁达的诗:“我孤单如一条隧道,群鸟从我这里逃脱。”
“我孤单如一条隧道”,只是一句简单的比喻,这里“孤单”和“隧道”之间的空白,本身就比“孤单”和“小草”之间的大。然而更上层次的是后一句,“群鸟从我这里逃脱”,它有些莫名其妙,但诗意却跳跃而出。
不像蠢诗的桥梁:直达对岸、索然无味;不像闷诗的迷宫:让你句句不懂、困死其中;好诗是一种气味,让你每一缕都嗅进鼻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气味散去你已身在别处,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总之,能量守恒,容器有限,一个“意义”的山峰耸起,必然把土尘四处聚拢,使得周遭变成一片空洞。而如果我们有勇气砸出一个“空洞”,反而有可能使周围的意义耸起。
让我们从自己的心窝砸起,只有这样,生活的那个巨大空洞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我们捕捉。
4、
在时间板块中的削平剁小。
在一次关于《贵妇与公爵》的访谈中,侯麦谈到:“我更喜欢缩小的影片主题,把它局限在公爵与英国贵妇的关系上,因为这一关系已经相当复杂了。”
男女关系而已,侯麦把它看那么复杂,只是因为文人的多愁善感吗?
这背后其实是侯麦对于时间处理的一个策略,它的本质是在有限的“电影时间”里,将“故事时间”缩小,“板块时间”变长,使得作者拥有更多的精力去描述事物的细部。
这方面的极致是《克莱尔的膝盖》,主线仅仅是一个男人想要抚摸一个女人的膝盖,一个甚至都不能引发感官欲望的身体部位。
侯麦一切取中庸,不写边缘化的人物,在空间背景上回避观光客视角,在时间背景上也回避那些标签性的东西。去除强烈的戏剧性,侯麦用他心思锐利的小刀,将生活这粒芝麻,切分出层次来,在大片的灰色地带中寻求渐变。
当然,这种压低情节曲线的波峰波谷、向生活轴线渐近的做法,会导致速度变缓、心理周期变长。对于很多喜欢坐情节剧过山车的观众,侯麦这样长段长段的缓坡,是很容易让人没有耐心体会到微妙的动态,就睡了过去。
不可否认,在商业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仍然是最有效的手段。虽然对于节奏的追求,容易导致高低起伏之间,缺乏合理而弹性的阶梯,留下为波折而波折的硬伤。可是观众觉得电影本来就是假的,会主动去填补那些漏洞。大阶梯的显眼,使得粗枝大叶的观众也能简单、片面、速食地享受“解读叙事意义”的审美愉悦,编剧也将大部分精力抽去用于弥补逻辑性的不足。
相比起来,侯麦就幸福得多,可以悠哉游哉的,反而去制造逻辑性的悖论,去经营故事的韵味。这就是侯麦的另一个隐性目的:他给人造成一种日常、亲切、细腻的幻觉,自然主义的假象,然而实际上,却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偷偷的去颠覆这一切。
此外,时间的缩小,势必引起空间的增长。虽然我在这里谈的都是时间问题,但是在导演观念和技法上,侯麦是一个真正的空间导演,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5、
在叙述逻辑里的自我反对。
如果说侯麦是用摄影机写诗的话,那么他是个使用长句的人。
侯麦的长句往往追求一种繁复的变化,在广阔的江面泛着涟漪,其目的是在一个稳定的结构内部不断瓦解结构,使得观者一旦进入这个万花筒,便被巨大无形的不能承受的美感所压迫而迷失。此外,也让故事不那么故事,增加故事以外的东西。
例如,他最具有标志的日记体,以一种貌似真实的叙述方式取得观众的移情。但是别忘了,对自己日记撒谎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小说家与读者之间的契约应该从一开始就建立。”(米兰•昆德拉)。可以说,侯麦首先用他的故事+镜语与观众建立了一个自然主义的默契,然后暗自撕毁这个契约。——他通过这种“不道德”来达到艺术上的道德。
他说:“我可以怀疑而且我一直怀疑这一叙事的真实性。”
从对白到情节,侯麦追求一个题目下的不断离题,甚至连题目都作手脚(《飞行员的妻子》)。侯麦不仅在大的枝蔓上搭成“空洞”,在小的叶子上也镂出“空洞”。
和荒诞派有所区别的是,他们的“自我反对”有些标榜的味道,好像是“你看,我在拍电影,电影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荒诞反而消磨了荒诞。侯麦选择自然态的叙述方式,甚至用闭合结构的大锅将他的故事装进来(《冬天的故事》),但你仍然在时间流淌中感觉到它的开放,这口大锅里沸腾的水。
顺便谈谈我对“零度表演”的看法。以往大家在反对模式化表演的时候,矫枉过正,认为不表演就比表演好。这对于一个依赖组接的较短镜头是适用的,然而对于一个依赖时间流淌的较长镜头,则往往显出人物的呆滞。事实上,一个影片所能承受的人物“维度”是有限的,不能为了让人物“多维”而“无维”。不如将演员置于交融的情景之中,让他信仰的同时让他怀疑,那么他的选择将不那么果断。眼神的游离,会显得演员的内心有内容。
6、
对白是侯麦达到“自我反对”的重要手段,所以我把它单独拎出来谈。
侯麦的对白,既能达到精确,又能达到模糊,这与他对主题的思考是一致的,他拍的是真正的“谈恋爱”的电影。(注意,是“谈恋爱”,不是“恋爱”。)
人们常说“爱情是不需要理由的”,不需要理由是因为理由太复杂,混杂了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因素,所以很难道得清。
爱的本质也许是“无私”、是“忘我”,然而每一个恋爱中的动物又不免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他们的勇气也来源于对于对方勇气的观察。正是这种观察,破坏了 “无私”本身。向外的力量和向内的力量牵扯,造成了恋爱的痛苦。除非一个人彻底自私,他才不会受伤害;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一个彻底忘我的人才享受痛苦的幸福。
然而,这两点,对于侯麦理性的主人翁们很难办到。理性的人很难“忘我”,(《女收藏家》里详尽描绘了这种欲望进退的过程),当然,理性的人也不会允许自己彻底自私,否则,那和理性衍生的“公平”有悖。
结果,他们就在不断地与猎物交谈,用交谈的方式犹豫、判断、自言自语。——“恋爱”,是纯洁的;但是“谈恋爱”,却容易浑浊,而且越谈越浑浊。侯麦的主人翁们说不清楚还偏要说,不讲道理还偏要讲,追求真理却一步步远离真相,追求自由却一点点带来束缚。
这就是视觉语言上,侯麦大多数采取中近景的原因,否则远观使人清醒。如果用侯孝贤那种“冷眼看人生”的远镜头来观察爱情,这个最复杂的东西也会变得最肤浅,从而丧失“真实”的迷惑性。
侯麦的电影,经常涉及到烂大街的“第三者”桥段。爱情,原本是悬在两人头顶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是高于他们两人的,是一种理想)。但是,当三人关系出现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分析其他两个人,这时,爱情便被拉了下来,甚至俯视。
俯视使得上帝产生,一个恋爱的上帝,一边在生活一边在认识自己生活的上帝;或者说一个编剧诞生,一个舞台上的编剧,一边表演一边写着台词的编剧。
行动会改变他的认识,认识又会影响他的行动;游戏带来老练,老练则痛失游戏的快感。
所以侯麦说:“我的影片主角,有点像唐•吉诃德,他们把自己当作小说人物,但是,有可能根本没有小说存在。”
这也就是视觉语言上,侯麦大多采取平视的原因。平视爱情,杜绝美化,使得每个人在空间上占据同等的位置,才能更为客观地描述个人和他人的关系。
侯麦的电影是知性的,我们喜欢跟着他的人物在公园、在咖啡馆、在沙滩坐下来,轻言细语地讨论爱情,像是听我们的朋友娓娓倾诉心事。我们逐渐被这个貌似冷静的水妖诱骗,走入水底。到最后发现话语不代表我们轻盈的灵魂,而是我们沉重的肉身。此时,他已用那潮湿的水草将我们缠得透不过气来。
 7、
7、
现在我重点来谈侯麦的视听。
如果,侯麦只是个编剧,那么,他将没有现在这么伟大,因为,优秀的小说家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导演,侯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而且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将两者结合得非常紧密。
一如你所听,侯麦是个罗嗦的导演,如果用日本漫画记录他的故事的话,想必有许多圈圈,围住一大堆密密麻麻的文字。
一些分析侯麦的文章,将侯麦的话语抬到比画面还重的位置,这是不对的。
侯麦是一个空间导演,他第一篇电影评论便是《电影,空间的艺术》。在空间观念上,他和巴赞是一致的,“感性的真实性首先来自空间的真实”。(当然,也有《威尔士人拜尔斯瓦尔》、《贵妇与公爵》这样的实验)。更多的,是用摄影的现实主义,把空间的抽象化程度降低,模拟还原“现实”。他的人物不会像巴顿一样站在巨大的国旗下,癫狂的发表爱国演说。
侯麦重视电影摄影的“建筑性”甚于电影摄影的“绘画性”。他的电影很难找出一幅精心雕琢的美景来做海报。这与他的市民喜好有关,更加重视人际关系,而非人与自然的关系。摒弃单个镜头的造型学,使得侯麦更有精力关注人际空间。
“叙事电影不是文学”、“叙事电影更适合展现动作而非语言”是现在经常说的话,这些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只是不能一概而论。
目前,我们对于电影动作的认识还是有简单化的倾向。试想,一个关注人际关系的电影,那肯定不是武打、追车、放风筝的特长。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说话,只有在说话的前提下才有动作。侯麦影片里的废话只是假象,它们是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依据。侯麦之所以极其赞赏有声片的发明,就是因为这一发明把影像从需求表意的努力中解救出来,把符号还给语言。
侯麦场面调度的常规方式是,人物扎在一块儿就聊天,他用中近景把每一个人都均匀地框着,人与人之间保持相同的距离,使得他们在空间政治的博弈上拥有均衡的筹码。然后,他观察一个人走进一个人的空间,或者一个人离开一个人的空间,以此观察欲望的追逐与闪躲。
平行调度的通常形式,是利用画框进行人际关系分配。在“推、拉、摇、移、俯、仰”这些调度方式中,比较具有侯麦特色的,是“摇”。侯麦尽量抛弃带有主观和机械色彩“推拉”,又不同于安东尼奥尼式的“移”,也避免好莱坞表意直白的“俯仰”。侯麦就是个三脚架,他是一个固守本位,站在一旁,摇头晃脑的观察者。
纵深调度的通常形式,是利用透视进行人际关系分配。最具有侯麦特色的,是正反打调度。他的正反打调度真正地突破了戏剧的一面墙,走上四面的舞台。安东尼奥尼利用建筑物的阻挡和视线的回避,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断,而在侯麦的正反打里(本来是用于交流的正反打),人与人的注视就是隔断。一个人物为什么要走开?既然走开了为什么要回头把视线缝合起来?不断的使用理性话语来维护自己的非理性,在道理和情欲间不断厮杀,话和话粘乎乎的粘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遥远,侯麦的正反打也越来越像诡辩,显示正是沟通使得我们隔绝。
这就是为什么,表面上最多的话语反而是其次的,侯麦说:“我首先是个默片导演”,“给我的人物一匹马,它就是西部片。”
如同波德莱尔,侯麦在书写最放荡不羁的内容时,也保持着节律。他看似禁欲的镜头,同时也是淫秽的:画框与人物的关系,是男女生殖器的关系,观察的是进进出出。
美术背景的实和话语的虚。话语的实和心理的虚。心理的实和行动的虚。行动的实和话语的虚。包裹着这一切的,又是一个看似真实的美术背景。
最后,侯麦影片中人物的话语,不仅消融于戏剧情境之中,也消融于场面调度里。我们只是看着这些思想大于行动,说着滔滔不绝的废话的哈姆雷特们,焦躁不安地,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里走来走去。
8、
最后,我要谈到意识形态,这既是叙事的出发点,又是终结点。
中世纪诗人但丁,在他惩恶劝善的长诗《神曲》里,详尽地描述了 “地狱—炼狱—天堂”的世界观。但是,他把不发表意见的中间派,放到了地狱的外层,一个“准地狱”。也就是说,连进地狱的资格都没有,永远无法获得拯救。
“……这凄惨的呼声
发自那些悲哀的灵魂,
他们生前不曾受到称赞,也未留下骂名。
混杂在这可鄙的合唱当中,还有一些天使,
他们不曾忠于上帝,但也不背叛上帝,
他们一心考虑的只有自己。
上天把他们驱逐出去,以免失去上天的美丽,
而万丈深渊的地狱也不愿收留他们……”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勇于走入这一层“准地狱”,生活不似但丁有头有尾的天堂地狱,人间的妖魔鬼怪都是从如来那里逃出来。在今天,一切价值观都在等待证伪,已经有太多粗暴的答案值得我们怀疑。
当然,你也可以怀疑“怀疑”,你还可以怀疑“怀疑‘怀疑’”……当文字循环下去,每一个引号都让我们不堪重负。
的确,怀疑腐蚀了我们的时代,罗伯特•麦基在《故事》里这样说道:“故事衰落的终极原因是深层的。……我们的时代变成了一个在道德和伦理上越来越玩世不恭的、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时代——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这种价值观的腐蚀便带来了与之相应的故事的腐蚀。和过去的作家不同的是,我们无从假定。我们首先必须深入地挖掘生活,找出新的见解、新的价值和意义。然后创造出一个故事载体,向一个越来越不可知的世界来表达我们的理解。这绝非易事。”
然而,当我们在故事里,对伦理进行每一次固定时,都应该小心的认识到,顿悟只是暂时的。电影好像偏爱傻子形象——阿甘、秋菊等,但是写故事的人,却不能一根筋。简单粗暴只能呈现为故事的气质,无法作为写作的方法。伦理在社会中需要固定,故事却需要保持它的独立性,讲述伦理的故事并不是服务于伦理的。
“追求多义性”是审查机构最怕的东西,他们最不需要有血有肉的人物。作为对地狱和天堂的“报复”,这一层“准地狱”同样不准道德挤进门来。艺术家必须使作品里的人物恢复成为自主的、建立在自己的道德之上的人。这是写戏者的职业道德。因为“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昆德拉)
说到底,电影不是朋克,不是政治。苦难的亚洲电影人,往往容易将电影工具化,在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时,丧失其艺术独立性。中国电影的百年疲软,最大的阻碍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叙事暧昧性塑造手艺的遗失,和对视听语言基本功的漠视。
诗人杨万里说得好:“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诗意的暧昧是我们手艺人值得追求的目标。相对主义的“准地狱”其实既是感性写作者的痛苦地狱,也是以幽默和想象力写作者的幸福天堂。
看似感性的侯麦就是个这样一个头脑清醒、手艺精湛的“骑墙派”艺术家,犹豫不决是他人物的主要特征。与雷诺阿表现人民的《马赛曲》不同,侯麦在2001 年的《贵妇与公爵》中描绘了一个与革命派(奥尔良公爵)交往密切的保皇派(英国贵妇)。在《电影手册》关于此片的访谈中,侯麦说了如下的话:“我没有打算采取什么政治立场,站在一边或者站在另一边。我的意图不在于此,而是继续通过电影使观众对历史保持一种趣味。……看了所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电影,我变成了保皇派。因为我想,这些影片中只表现人民,优秀的人民。很好,但也需要表现其他的人。”
在我看来,这就是“戏”的终极精神——体贴每一个角色,站在他(她、它)的角度考虑,最后方能以达观的态度,消解偏执的痛苦,享受生活的乐趣。
从三个系列的作品来看,侯麦的叙述手段逐渐从主观性小说走入客观性戏剧、从画外旁白走向人物间的自由交流、从男性视角更多地走向女性视角。就是为了更加设身处地的替人物着想,从而更好的反观自己。在逐步用悲剧完成他的感性诉求后,他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像喜剧的狂欢,从头脑发热的恋爱,到有距离的调情。
很多人讶异于侯麦76岁时还能拍出《夏天》那样青春的电影,然而我想说,年轻的人永远年轻。《夏天》最青春的是什么?——是那些穿着比基尼的少女?是那些谈恋爱的甜言蜜语?——都不是。
《夏天》最青春的是那份年轻人永远的迷茫;是在摇摆不定中,迟迟不肯选择的那份怀疑精神。
拍了四十多年戏的侯麦,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在讲着相同的主题。早已过了青春期的人,为什么在欲望问题上还是跨不过去?其实他就是那个摇头晃脑的三脚架,在蠢蠢欲动的柔弱之下,有着最清醒的坚定,这份清醒就是——我不明白。
如果一个事情,作者搞懂了,还有什么必要拍呢?
侯麦说:“我想,拍上一系列的道德剧,譬如说拍它6部,观众和制片人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我的想法了。我从不去猜测观众对什么题材最感兴趣,我只是将同一主题反复处理六遍。不管怎么样,拍到第六次,观众总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一旦想好,我就毫不动摇。只要坚守自己的信念,终究会有人支持你的。”
虽然电影是工业,然而这工业贩卖的是个性。观众是消费艺术品的不同,而不是消费陈词滥调。任何创作者都必要张扬自己的个性,都有义务张扬。即使是张扬自己的沉默,张扬自己的克制。作到极致是艺术家的必备情操。侯麦张扬的便是他最清醒的困惑,这是他最宝贵的品质。
威尼斯电影节在授予侯麦终身成就奖时,给与这位“脱离时代的保守主义者”这样的评价——“在记录时代的社会意义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他并不是想记录什么时代,只是在沙滩上散步聊天,半固执半游戏的等待着他的绿光而已。
顺带说一句,侯麦电影的结尾一般不会像我这样煽情,他一般都是,嘎然而止。
主要参考片目:
六个道德故事(1962—1972):
1962《蒙梭的女面包师》Boulangère de Monceau, La
1963《苏珊娜的职业》Carrière de Suzanne, La
1966《女收藏家》Collectionneuse, La
1969《我那一夜在莫德家》Ma nuit chez Maud
1979《克莱尔之膝》Genou de Claire, Le
1972《午后之爱》Amour l’après-midi, L’
喜剧和谚语集(1981—1987):
1980《飞行员的妻子》Femme de l’aviateur, La
1982《好姻缘》Beau mariage, Le
1983《沙滩上的宝莲》Pauline à la plage
1984《圆月映花都》Nuits de la pleine lune, Les
1986《绿光》Rayon vert, Le
1987《女朋友的男朋友》Ami de mon amie, L’
四季故事(1990-1998):
1990《春天的故事》Conte de printemps
1991《冬天的故事》Conte d’hiver
1996《夏天的故事》Conte d’été
1998《秋天的故事》Conte d’automne
(插图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