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之于我,就是一种欢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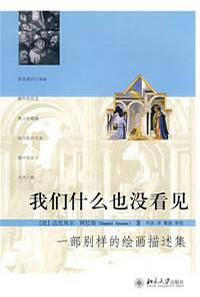 文:肥内
文:肥内
虽然我从不怀疑自己之前的课程规划的初衷,但看到阿拉斯的这番话,无疑仍是一种鼓舞。我也想自豪地像他说出「不需要文字,就已能看见作品所要叙述的是什么」(页13),但「看见」仍有程度之别。可是诉诸于这种看见的,是一种最纯粹的直观。唯有在这种直观下,在与人讨论的过程中,才能知道自己与别人在思维上的差异在哪里,也就是说,这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骗不了人,但也因而骗不了自己。我才在想,作为课程规划人,我的立场反而因而吃亏了,因为我完全知道要放什么影片,我也因为要给大家一些讯息而收集数据,于是我也必定知道得比别人多,然而最后,究竟哪些是我自己的观点,哪些是从资料收集来的观点,我再也分不清了。课堂上,只有我一个人无法享受纯粹的直观。我所遭遇的,不是一部单纯的影片,还包含前人的读解讯息构成的信息网,甚至是我脑里自动启动的证实机制,用以核对哪些信息是可以获得证实,哪些又是可以用来向参加者说明分享的。我的观看已经不再纯粹了。
我常想起,当我看电影、学电影到一个疲乏的状态时,我老会拿起《去年在马里昂巴》(L’ 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来看,因为它是引领我进入电影世界的关键,是在观看它的那一个下午,让我完全沈醉,或者说震慑,在一种全然属于观看的欢愉之中。我丝毫不理解这部影片,或许我约略可以说一说我看到的「情节」,我却也是充满疑问的。所以,每当我对学电影有丝毫的疑惑时,我总乐意回到这部影片上,去找寻原初的动力。
我会想到欧弗斯(Max Ophuls),我会理解为何我之后也会被他的作品以及他对影像的追求所吸引,这是没有疑义的。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劳拉蒙黛丝》(Lola Montès),一部纯然属于观看的影片。但对于我来说,它所展现的视觉,又与雷奈(Alain Resnais)的不同。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劳拉蒙黛丝》时,我睡着了,我禁不起眼前这些绚烂,那些色彩,那些动态,以及大量的从手法中传来的讯息。我想起《阿玛迪斯》(Amadeus)中,国王对莫扎特(Mozart)音乐的抱怨:音符太多令人疲倦。欧弗斯的影像无疑也具有这种特征,要说起来,拿「巴洛克」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作品不但是贴切的,甚至是一把非常实用的钥匙。巴洛克首先先是一种观看的艺术。
这么一来,一位认为不必依循欧弗斯对电影看法的网友,他的质问就无可厚非了,本来就无须照着他的模式,但却不妨碍气味相投的人由此进入他的世界。
欧弗斯在一篇就叫做〈观看的欢愉——思考影片的对象问题〉的文章中也说,影片对他来说之所以成立,首先在于他能预视到合理的影像。巴洛克透过综合媒材的组合,也在于将观者直接拉进画中,这份专注,首先来自观看。
进而,阿拉斯在《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的第二篇文章〈蜗牛的目光〉,试图从德科萨(Francesco del Cossa)的一幅《天神报喜》(L’Annonciation)中一只非常突兀地存在画面下缘偏中的蜗牛,引导我们思考画家在布局时,所希望引导观者进入「观看世界」的用心与方法。这些画作(包括阿拉斯在文中举出的其它几个画家)都属于巴洛克前派,不过属于什么风格作品并不是我们首要关注的焦点,而是阿拉斯对于观看方式的思考。这只明显体积过大的蜗牛,最后在一连串不论是图像学(iconology)或者艺术史学研究的调查后,或许会因得出的结论是「它并非为我们指出要看的东西,而是告诉我们怎样去看所看到的东西」(页30)而让人大失所望,「大失所望」!?这可是历经多少智慧累积的眼光啊!
阿拉斯的分析,使我恍然大悟了,为何我们老觉得欧弗斯所构筑的画面中,老有一些条条杠杠遮在画面的前方,或许,他不像德科萨这般实验,将蜗牛这个画面中 的对象成为一个「在画面上」的对象,因而在我们注意到牠的时候,重新进入画中。好比波佐(Cassiano del Pozzo)在《咏赞圣依格纳提斯》(Glory of St. Ignatius)的那幅圆顶画作一样,我们再也分不清是画,是雕塑,还是柱,是艺术的幻觉将我们拉进那个神的荣耀,还是神迹本身将观者带到了一种超脱的感觉。这份幻觉所带来的迷醉感,即使只是透过书上的印刷,依旧能够打动人。这么说来,德科萨的手法可以说是有道理,且非常合情合理。而欧弗斯的巴洛克,同样透过这种方式,横横杠杠就是处于画面与视线中间的引导,遮档,反而让观者的意识更加急切地想冲破阻挡,终究,我们的完型心理会为我们补充这些遮挡,进而完成一个专属于观者的型。
可是,在受到精神上的感悟后,带来的便是一种迷幻的疲惫,根据这个,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创作了《圣特瑞莎的幻觉》(The Ecstasy of St. Teresa)。这同时也是我们观看欧弗斯的感受。然而,巴洛克将观者拉进的作品中,但终究要受到传统的约束,这种约束不是对于艺术的,而是观者的抗拒。这也是为何在捍卫所谓古典价值的人们眼里,巴洛克是歪曲的,是不完美的。
巴赞(André Bazin)在将《劳拉蒙黛丝》比作《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时,我想或许他只是着眼于影片「以各种方式」处理倒叙的这层关系(3),然而,《劳拉蒙黛丝》与《公民凯恩》同样在推出之时造成巨大的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歪曲不完美的珍珠啊(4)。
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人们对于观看居然有这么大的偏见。这也是为何在嫌恶巴洛克建 筑的歪曲,却仍不免要让那些造型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这也是为何就算得不到适切的解释,德科萨的蜗牛依然会不断萦绕观者心中一样。欧弗斯画面中的条条杠杠老将人搞恼,而让人抱怨画面怎么不干脆一些,但正是如此,这是一种巨大聚块的堆积,所有元素将群聚在一起,以最大的力量吸引观者的观看。这也是为何欧弗斯的真正接班人不是那些崇拜他摄影机运动的后继者,甚至也不是努力学习欧弗斯轻触的那些高雅影作,而是为了表达视觉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格林那威(Peter Greenway),可惜他要真能学到欧弗斯轻触该有多好。
于是作为一个观看欢愉的忠实信徒,我相信即使在熟悉的东西上,也是必须要添加一些,想尽办法,可以不断翻新、刺激观看的元素。我无法不想起巴赞在描述朗瓦(Henri Langlois)放映《吸血鬼》(Les Vampires)的方式如何使这样一部大家已经熟悉的影片,变得如此新颖,只因为朗瓦真正透析了这部影片,并非从内容,而是其形式与其语境的考察,但更多是想象力吧,我想,而造成的结果(5)。在参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放映影片,对我来说,若想获得观者的直接观看欢愉,这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观者要求事先获知下一次的放映,那么,对我来说,新的放映方式则不可少。一切只为了维持观者的观看欢愉。
这也是为何,在播放《秋天的故 事》(Conte d’automne)时,我拟将影片最末人员名单走马灯先放一遍,而第一遍放还得先将画面关掉,只留下片尾这个好听的音乐,然后再放一次片尾。然后便可以重新放映正片。这是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我可以让观者直接先熟悉侯麦(Eric Rohmer)设计画面的一个巧思:即他刻意而为的音画位移叙事。我希望观者注意到这片尾曲播放时(其画面是一个婚礼上的餐后舞会,有乐队演出,人们跳舞),听到吉他独奏时画面出现的是手风琴镜头,反之,手风琴独奏却出现吉他画面。然而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所以才要让观者先「只听音乐」,如此,先将乐器编曲的印象留给观者,而当有机会看到画面时,便会讶异音画的对立方式。然而,这也只是进入侯麦世界的其中一个途径而已。但我从不晓得自己对观看欢愉的执着是否能因而传达到每个观者。
只是,在阿拉斯尖锐的笔锋下,也不断令我反省自己。阿拉斯对那只蜗牛的研究,肯定要让我汗颜的,他说的没错,仅仅揪着一个明显的论证,并因而获得片面解释之后,就撒手不管了,这样的态度确实值得质疑。好比当我被质问《莫瑞尔》(Mureil)片末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长跟拍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除了片面提出解释外,还依赖于「雷奈是一个以玩笑态度拍片的人」为由,回避这个问题,这显然,我也犯了阿拉斯所批判的人的毛病。当我们急于用一个看似耸动的论述来回答某一个其实学问很深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逃避的是自己的不足遭遇这种难题的状态。是的,这是我的逃避,而我却从来不晓得,还以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已然令自己、令旁人都满意的答案,这也是为何,我老抓着雷奈影片中出现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人形这件事不放的理由了。我真笨,居然还要人家来提醒自己的无知。
看来,我得不断为自己开发新的是观看变得更加欢愉的方式。我回绝了主持影片分析课程的主持任务,因为我想要重新回到当观者的立场,或者说,找回这种权力。等着我不熟悉的影片进入我的眼里。或者,我不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我根本不应该写信给老师的。
1. 《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一部别样的绘画描述集》,原名「on n’y voit rien」,何蒨翻译,董强审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不过中文版中丝毫没有附上任何原著的资料,也就是说,不确定本书写成的年份为哪一年。
2. 本作品约绘制于1550年。由于本书是法文翻译过来的,故文中附上的画作原名也标以法文,由于眼前我网络使用不便,也无法搜寻正确的原画名,故本文中所有与阿拉斯的书有关的人名、作品名,一律采取书中附上的法文名。请各位明察。
3. 见《劳拉蒙黛丝》的剧本,由《前台》(L’Avant-scéne)出版,1969,一月号,第88期,页106。不过我不确定巴赞对这部片的完整评论如何,我只是从这书上一小段文字中推敲了巴赞的意思。
4. 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想到我这里的用法,便是取巴洛克baroque这个词在大部分的书中都追寻到伊比利半岛珠宝商的用词。可参考巴赞(Germain Bazin)的《巴洛克与洛可可》,王俊雄等译,台北:远流,1996,页1。
5. 有兴趣者,千万别错过在《电影是什么?》文集中的〈非纯电影辩〉这篇文章。参考版本可见崔君衍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页80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