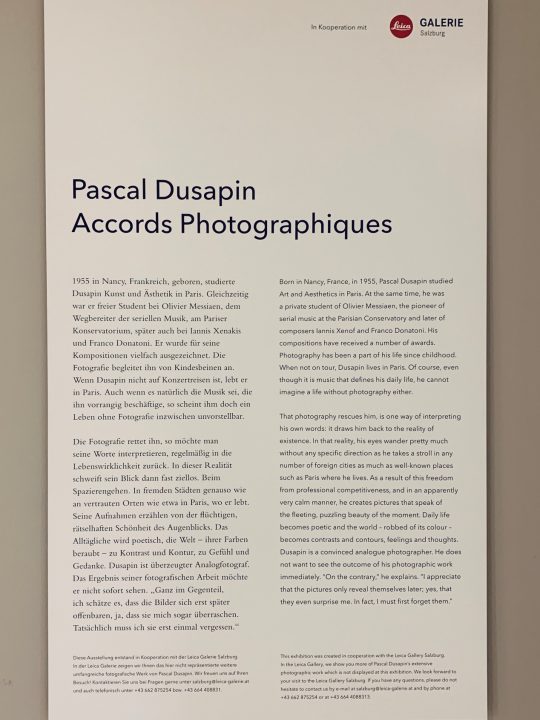2019现场二次体验
文 | zzzcat
从2019年初,我又开始无规律但不间断地记录一些日常。原因之一是想重建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且留存一些有趣而特殊的记忆。这些年工作中往往用的都是格式文本或者纯粹和数字打交道,真到了一张白纸一件事置于自己面前,却无从下笔。前两年看的某些演出,记忆中留下的除了音乐本身,还有很多细节也令人回味。例如,有一次半场休息时捡到了一只古旧皮夹子,而另一场中一位老人和我絮叨他独自从美国某港口坐船到英国南安普顿,而那天在Royal Opera House上演《罗恩格林》是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很遗憾,那些本应记下来的珍贵细节,都没有记录,可能到了下一个20s或30s,这些细节就成了遗忘。
到了2019年底,看到各种媒体上满眼“十大”遍地“最佳”,我也想过是否要把今年看过的三十多场排个先后。可惜做不到,也不愿意列出个“十大”。首先遇到的是一个排序标准依据的问题。大众点评与之餐厅可以从口味,环境,服务去打分,而演出是个全方位的个人体验,没法用细分到仅有的几条标准。即便是有了标准,评选、评星、打分还是得留给专业人士或者乐评人去做。作为普通爱好者,或者我更愿意把自己归为“体验者”,大多的印象都是来自纯主观感受,这怎么能够排序?
所以这里同大家分享的现场记录,是这一年以来让我有新知或是奇想的现场,纯粹的主观感受,而是否有名家名作或天团不是入选依据。当然,分享主观感受也存在一对矛盾点:这可以被读者认为是一堆废话,或是借由我的经验而产生读者的二次体验。假如是后者,那就太好了。这样,以下排序基本按照月份,只是把有段加了番外篇的留在了最后。好,坐好,放松。
1月 彼岸 – 俞湘君钢琴超媒体音乐会
大型“艺术装置”现场
将凯奇、阿德斯、贝尔格、考埃尔等人的曲子凑在一场音乐会,在上海算少见。且这场还不算传统的钢琴独奏,三种表现元素 – 钢琴、现代舞、光来表达音乐的美感舞台上两架钢琴 – 一架普通三角钢琴,一架预制钢琴,还有几套LED灯柱和几盏追光灯。灯光,在前几曲子完全属于可有可无地打着、追着、闪着,看似完全无序,也没有与音乐融合。而现代舞者和钢琴家的交流限于换位、换谱、绕圈,躺在钢琴底下的一霎那,让我想到了钢琴家和她的动物伴侣的日常。舞者的某些动作,特别是对着观众“来吧来吧”的那个手势也太具象,这限制了音乐表达,声光舞编配需要给观众留下的想象空间就完全被填满。而转折出现在第二首需要弹奏预制钢琴的凯奇的《奏鸣曲与间奏曲第十六首》,钢琴暗哑的金属色调和交替出现投影在舞台背景的黄色灯光,好似观众正坐在一个石窟中的水池边,看着灯光照射下的水波反射在石壁上,水珠从钟乳石尖不断滴入水池的声音在四周回荡。这时候的钢琴和灯光形成了一个融洽的装置,整个体验的产生缺一不可。而同样在倒数第三首考埃尔的《女妖》,灯光投影出静止的玫红色对称弧形,演奏者婀娜地趴在三角钢上拨弄琴弦,而舞者作为一个安静的旁观者,站在琴边,成为了一个交流的通道 – 链接了台上、台下、观众、演奏者、钢琴和灯光布置的场景,又一次把舞台音乐观众融成了一个整体体验。
后来想到这样的音乐会比较适合在环形音乐厅举行,例如上交,而非鞋盒型的上海音乐厅。这样观众属于“围观”,而灯光可以照射到360度,融入感更好。亦或是有一天,类似“艺术装置”的音乐会可以移到某类穹顶建筑,甚至是噪音测试房(我又想野了),把里头的吸音墙蒙上黑色幕布,钢琴放在中间,观众围坐在琴边,外围装置灯光。那一定会有趣。
3月 上海交响乐团18-19团厅音乐季 余隆演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却是去听《江城子》
陈其钢的曲子听得不多,印象完全始于北京奥运会的《我和你》以及《蝶恋花》,国内作曲家一直是我的全盲点。《江城子》的圆号开篇而弦乐气若游丝的演奏,画出灰白薄纱一幅,分割梦醒之间,也是阴阳两界。合唱融于乐队,而没有常规的主奏乐器,京腔女高音念白,确是整个乐队的主奏乐器。
京腔念唱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一停一顿,游弋于乐队和合唱编织的薄纱之间,清晰,好似进入梦境时的难辨真假。在接近二分一时,乐队和合唱渐强、铜管乐器加入、织体慢慢厚实,京腔念白和乐队的对峙变得势均力敌,而灰白的纱被织成了一块厚重满是阴影的布,随时掩盖女声,安静,浮出水面,却又沉入梦境。到接近结尾处,乐队及合唱再度淹没女声,而她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地想穿透那块布围裹的梦境,两界 – 伸出手、抓住虚无、而被淹没。合唱中男声的对答,荒凉而无能为力,最后所有的最强音停留在了那里,犹如突然从梦中惊醒双眼睁开看到的日光惨白。同时间乐队转弱,散开,游丝般离去。的确好久没有听到如此震撼的新作。情绪起伏明显却不突兀以及运用人声作为乐器,都十分精彩。
中场时候去买了张NCPA出的《江城子》,就收录了这一部作品(怎么现在都爱出单曲碟?)- 还包括了DVD以及陈对这支作品的几段实验录音。封面、封底以及唱片小册子都运用了灰蓝主色 – 阴郁湖蓝色。而封面上有一缕柔粉色光晕,同样在唱片上点缀了两条粉色去呼应,精彩。小册子纸质精良,页内字体细而清晰(我喜欢小字体的书和册)。其中有由陈其钢自写的作品背景,乐评人焦元溥的作曲家和作品介绍,以及乐团和表演者的简介(中英文双语),可谓业界良心。
3月 上海交响乐团18-19团厅音乐季 斯拉特金与SSO
D区5排1座的山顶正中位
因为早先在油管上看了斯拉特金好几期的Leonard Slatkin’s Conducting School,风趣幽默、简单易懂,看着看着老爷子成了熟人熟脸。但也不想在这场上花太多钱,那就预先买了张山顶票。
斯拉特金开场来了个巴赫《小赋格》,斯托科夫斯基的管弦乐版,一点都不“小”却有点“短”。而我完全没有听进去,从老爷子上场到这首小赋格结束,我却一直在脑补科普兰的Rodeo, 因为每次斯拉特金的那个油管节目开场,他都踏着Rodeo上场,直到指挥台上站稳当。
第二首曲目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结束后,小提琴家Bendix-Balgley加演第二首巴赫的Partita。这时,D区5排1座的山顶正中位开始显现180元“神迹”。闭上眼睛听到的琴音好似在教堂,或者记忆中的某栋老宅,声音清澈,飘于空中,那是时间和空间给予的发酵。
下半场演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曾经家里的盗版安德烈·普列文和伦敦交响乐团的那套碟是我对这部交响乐的启蒙,且后来又听到了第三乐章被截取且改编为流行歌曲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第三乐章烂熟到连坐在我一座之隔的阿叔都可以从头哼唱到尾(遭我三四次白眼)。斯拉特金手势简练,cue in乐器的动作十分清晰及时,全曲都为背谱指挥。整个曲子除了第一乐章开始的几小节稍微卡得有点太脆,第二乐章管乐发了一个怪异的音(不是指挥的问题),其余部分简直不像是上交在演出。第三乐章时,他将指挥棒轻轻地放在了大提的谱架上,双手翻空。节奏快慢声音强弱收放自如,填充到整个音乐厅刚刚好。能听到绵延乡愁,时而又好似黑白电影配乐弦乐的尾音。最可怕的是,这一次算是把上交习惯性的所有声部都一个响儿的毛病也治了。不知道是D区5排1座的山顶正中位的原因? 还是真的演奏出了该有的层次,一个小时一曲完结,好多乐迷都起立叫好,斯拉特金被唤出谢幕三次。
看完走回环贸和家人汇合(他们逛店聊天到10:30)家人说我脸色好似春风拂面。
再提一句,D区5排1座的额外好处,就是可以把外套好似晾衣服一样挂在背后栏杆上,因为这是音乐厅最后一排(不良行为乐迷,减十分)。
5月 Steve Smith纽约四重奏
非·老年爵士乐队
Steve Smith的这场演出的中的“纽约四重奏”实为他自己的一个assemble – Vital Information NYC。
演出结束后,我和家人在大厅外看到等待Steve Smith的签名队伍已经排成了长方形的长宽两条边。而我们站在了签名桌不远处瞄着,想从近处看下这位能把鼓打得好似人间奇迹的老爷子的真容。没过多久,老爷子就走到了签名桌前坐下,他的VI NYC的朋友们没来,还是穿着演出台上的那件蓝色花衬衫,挂着金链子,光溜溜的头顶上还有汗珠,面色绯红。每位观众递上来的唱片,他的书Pathway Motions,甚至是T-shirt,老爷子都极其认真地签了,沉着而面带微笑,根本看不出几分钟前刚刚酣畅淋漓地打完了一整场。
家人问我,Steve Smith今年贵庚?呃,六十多了吧。其实VI的键盘手Mark Soskin, 吉他Vinny Valentino也都是这个年龄段了,而贝斯也差不多,这立马让我想到了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而这四位六十左右的朋友演出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Steve Smith进入状态很快,两首一过已经伸展开松弛地左右开打。而键盘手Mark第一首的某段落还有稍慢于鼓点节奏,却被他老道的经验“掩盖”- 弹一段,起身向观众挥个手,一个loop过后就节奏回来了。然后继续向观众挥手。第一曲以Steve老爷子的solo结尾,邻座陌生妹子说了两字“神呐”。
嗓音很有质感的Vinny在第三第四首和Steve演起了南印度的vocal percussion – Konnakol, 也就是用人声作为另外一件节律乐器发声而不带具体意义的唱词。嘀嗒咯哒咚这五个发音,按照不同的排序、节奏和长度,完成每一句唱词。这个形式组成的Jazz fusion,十分有趣,也得到了观众的共鸣,到了之后表演的Sixteen Tons和Slats基本都是观众鼓掌应和节奏,而乐队也乐于和观众互动来调动情绪。
期间Steve老爷子特意介绍了乐队的每个成员 – 两遍!而且在第二遍介绍的时候把成员之前和某些大牌的合作背景也稍做了交代。且若是改编曲目,也会清楚地告诉观众由哪位乐队成员完成。这种中心人物稍退一边,而让同伴站在台前的方式,令人敬佩。
音乐会结束前加演了两个有趣的节目。在第一个加演节目前舞台的灯光就暗了下来,Steve Smith掏出了两根发亮的鼓棒,搬了个碎音钹到舞台正中,由慢到快,不断变换节奏,且一边做出抛接鼓棒的杂耍动作。虽然期间鼓棒落地一次,大家也就是开心笑笑而已,本来加演就有很大的娱乐成分,而Steve老爷子在这个节目结束,就顺手把两根鼓棒都向后甩在了地上,全场又是会心的大笑。而第二个加演节目从远处看是用了类似鼓刷般的道具(但不是,看着像锅铲)耍了一遍小鼓?别怪我坐在半山的确看不清啊。
紧接关于“六十”的话题和家人边看别人签名边聊着。这个岁数的国内的艺术家大多都已经是台前大腹便便,幕后德艺双馨,开始政工教育工作,要不然就成了综艺秀的评委吧,哪儿还有这股劲儿和热力?别说六十多了,连小年轻年过三十,也都得把重心转到票子房子老婆孩子上去了吧?
“你看看丁俊晖这次斯诺克世锦赛那个状态,啧啧,打到第三四盘的都已经眼睛血红,长杆不准。缺乏训练啊。”
“对啊,看着以前那两代领军史蒂夫·戴维斯和斯蒂芬·亨德利四十多的状态就知道,人家的训练水准如何。”
对话扯得有点远了。这个话题已经从艺术范畴转向了生活范畴 – 而这两者却有一个词是相互共同的 – 纯粹。而这又让我想起某指挥家在年轻时的一段采访:“你现在已经有了国际知名度,也有了个好乐队,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某指挥思考了一秒说:“Musik.”
9月The Party is Over – Weimar Berlin Series by Philharmonia Orchestra
乐评人的现场
昨晚坐在我前排的是两位白发老先生,估计都是乐评人,我姑且称他们为五湖四海先生和发模先生。
五湖四海先生:
完全没有发型,而鹰钩鼻和棕色的褶子脸显示着祖上一定来自五湖四海。身着休闲卡其夹克,牛仔裤,乐福鞋。女伴,应该是妻子,因为先生的无名指有金色戒指,也是五湖四海脸型,漂亮的黑色头发在第二曲魏尔的Concerto for violin and wind orchestra时斜垂下来,在一声强音后才抬起了头。
发模先生:
坐在我左前方的那位,银白色的分头完全没有英国人惯常的脱发问题,我想他下雨一定打伞,洗头一定用护发素,且定期洗剪吹。灰色呢子西装,灯芯绒裤,皮鞋虽见年月却保养极好。老先生是一人来听音乐会,他隔壁的位置空着,不能确定他是买了一张票,还是他的伴儿没有一起来。
两位老先生都拿着笔,在演出之间不时记录。
五湖四海用一支圆珠笔记录在节目册上的顶端。记录的不多,每乐章也就两三次,大多都是速度节奏变化时。想凑近去看到底记录了啥,却看不清那种扁平圆润的字迹。到了下半场贝尔格的Lulu Suite和欣德米特的Dances from Das Nusch-Nuschi,五湖四海基本就不动笔头了。
而发模记录的频率明显较多,无论是乐队在布索尼的Two Studies for Doktor Faust那温吞水结尾,或是Lulu Suite中女高音换气明显,都会记上一笔 – 在另外一张演出人员名单上。
这两位在对乐队鼓掌的态度上也是完全不同。发模先生是极其吝啬,鼓掌两三下就又正襟危坐。甚至在Christian Tetzlaff加演巴赫 Partita in Em后都没有鼓掌,当然Tetzlaff的巴赫随意轻狂了些。五湖四海先生明显热情得多。
估计一位是严肃乐评,本场三星。而五湖四海会是温和派给本场四星半?
本场Lulu Suite的女高音为美艳的Rebecca Nelsen。的确难为她了,在乐队前的一张椅子上干坐了第一段落,挤眉弄眼,没开唱就喝了两次水。第二段落站起来继续丰富的面部表情,第三段落Lied der Lulu才开唱,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之后的段落用怨恨的眼神看了指挥萨洛宁好长时间,好像他就是开膛手Jack或是Lulu她自己的人生。
剧作家或者是作曲家就爱写这样阅历丰富、精力充沛且永不满足的女子,这样的人生似乎代表着女子真实、敢爱、个性独立、难以驯服,但往往结局惨淡。倾慕这类女子,却认为自己掌控不了,把她写惨了,说白了就是如此 – 艺术家文人的上帝视角小伎俩。
唱词十分有趣(那就是女子们把话挑明了说):
“You know very well why you made me your wife,
as much as I knew why I took you for my husband.”
“If you say you sacrificed your golden days for me,
remember that you took away my entire youth。”
“I have never in the world wished to seem to be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 am taken for,
and I have never in the world been taken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 am.”
10月 艾莉索·维莎拉兹钢琴独奏音乐会
老法师的演绎
今夏在萨尔斯堡旅行时的住处,女主人叫Sarah,三个孩子的母亲,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从瑞士苏黎世搬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把老宅改造成她喜欢的模样,作为酒店公寓。
公寓里估计有三四架三角钢琴,餐厅就有一架。每天早饭的时候她都会和我聊一会儿。
8月1日那天早上,她问我晚上去看哪场。我说去看索神啊。她顿时来劲儿了。
“他们这批是真正的老法师(请允许我把old school master译为老法师)啊!我的老师曾和我说,某某某(不好意思,我没有能get到那位的名字)在上场前,还会好好沐浴,让自己有净化的心灵。”她之后有说了很多,似为了让我做好准备,去接受一种不同于当今钢琴红人的老法师现场风格。
那晚的现场,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索科洛夫对作品的演绎 – 质朴大度,而是索科洛夫上台和下台,走路只动腿,身体的其他部分,完全没动 – 他弹琴大致也如此;以及,演出是在Grosses Festspielhaus,而我坐在第19排,但是完全听不出琴声有遥远,或是“飘”的感觉。
关于这两点,10月27日下午的那场艾莉索·维莎拉兹独奏,使我有了更多的理解,以及对Sarah提到的那些老法师的特色有了进一步(还是初步)的观察。
首先,关于在不同的音乐厅的声音控制。上交属于中型场,我坐在F区第4排。琴声是如此饱满,同样的没有任何疏离感,没有“飘”。无论是弱音,还是如普罗科菲耶夫那把钢琴当打击乐器耍的Toccata,都十分完美。可能是上交还不够大,那盐堡的Grosses Festspielhaus又如何说。F区4排或19排都算是距离稍远,而曾经三次在不同场地和远近听特里福诺夫都完全达不到如此效果。
对声音的控制,不光是在对声音于空间中的“量”的控制,好似去做风衣对设备电平调节,也是对于声音从有到无的控制。Music is the silence between notes。好几次注意到维莎拉兹在一段落结束后,等待尾音到消失,而并不是等到完全消失,就开始弹奏下一段落,而且开始弹奏的那个时间点的尾音响轻,都是等量的,十分统一。不知道是否是每一段落之间隙的时值在乐谱上有规定?取决于踏板控制之类的凡人不能理解的技巧?还是她本人的一个习惯? 这样的声音在消失的过程中,接着下一个音,在现场听得十分清晰,而唱片却没有如此效果。
维莎拉兹某些弹奏时的姿势,也很统一。这个在舒曼的《新事曲》第八首,有一小段的重复四遍中,她右手的抬手动作,高度,时间,完全一致。伴随着身体随着节奏的微微前倾,导致我脑海里有个印象,一定是个迪斯科美女,若在莫斯科有迪厅的话。这应该是已经对曲子的熟悉和控制达到了肌肉反射的程度。记得某文中也提到过有人观察古尔德在不同场合中弹奏同一段落时,抬手高度也有类似的统一性。
除了这些弹奏时候的略微前倾,侧摆,抬手以外,迪厅美女在钢琴后,基本就没什么表情和动作了。这也和索科洛夫非常相似。若是坐在钢琴右侧,只看到她上身的话,那就是天鹅游水。
而在音乐里的情绪表达也不会是情感泛滥。之前听过某张碟里维莎拉兹弹肖邦夜曲,马祖卡,华尔兹,甚至有些粗粝和爽朗。而这次现场的第一首老柴《四季》的第一首《炉火》就把我听得鼻子酸了下 – 完全是冬日夜晚,屋外飘雪,屋内炉火映在墙上,噼啪的火星,亲人或爱人依偎,几只靠垫,席地而坐。温暖的声音。反而第六首《船歌》就很直叙,可能外面听到的糖精片太多了。而上半场的两首普罗科菲耶夫造成了很多中场休息时乐迷出来狂抢她的碟,“我要普罗科菲的那张”。大概乐迷这样省去作曲家的名字中两个字,可以说的快些。特别是Toccata,虽然她的弹奏速度并不如阿姐年轻时如此无敌之快,也没有霍洛维茨的泰山压顶之感。但这首炫技的作品很容易弹糟糕,弹到令人感觉敲墙板式的乏味。避免此类乏味,曾在采访中维莎拉兹提到了”弹性速度”,就是tempo rubato或者rubato。偷时间,或者细微的节奏变化。“如果观众能够察觉,那就是‘渐快’或‘渐慢’,无法被察觉到的速度改变才是真正的弹性速度。”她提到最需要以弹性速度演奏的便是巴赫。“如果巴赫没有弹性速度,听起来会极其无趣,永远在重复。” 这个不让人察觉的技巧,据说只靠天赋。可能阅历也有影响吧。好似听音乐 – 并不一定是完全被动的行为,而也是个主动接收的过程。而这个”接收”,能接收到什么,的确需要时间和积累。
一连串的经历 – 和Sarah聊天,混混沌沌听索科洛夫现场,电视上看斯柯达的大师课,去现场听维莎拉兹,这些让我意识到,之前十几年的钢琴碟和现场好似白听。一些细微而含蓄,怀石料理般看似寡淡,却暗藏精致的意味,直到最近才慢慢领会。我也应该“好好沐浴”,开始聆听“老法师”们的演绎了。
11月 Akhnaten
歌剧,或成受众最广的严肃艺术形式
The Met Opera上演的格拉斯的歌剧Akhnaten,若有能力“拉片”的话,可以说出好多个中道理,而我只能一窥大概。
序曲的舞台效果好似剪影。人物都在幕布后活动。舞台的纵轴被划分为三区,最高区的剪影们的头部为动物造型,和内行讨论后才领悟到这可能代表着当时埃及的多神制(宗教),而在歌剧最后一幕,最高区坐着一群听讲座飞纸飞机的考古学者(科学)。
可惜序曲中某段小号和乐队的节奏好像有点岔开了,对节奏的控制没有Stuttgart State Opera的那版录音来的精准。序曲部分的音量也比较弱。
第一幕的第二场可谓男主未开嗓先惊人。Akhnaten的扮演者是假声男高音Anthony Roth Costanzo, 在这一场中他有全裸演出,而且是台上的舞者(十个人的杂耍团体)把他360度空中翻转,直接套入一条臀部宽大的裤子。这样完美的体型和肌肉力量很难想象是属于一位歌剧演员。当年Festival Aix版本的德彪西《佩桑》中,两主角也有全裸场景,但Barbara Hannigan用了替身,那是个很巧妙的安排,两位Mélisande正好展现了言行和性格的平行双重。第二场Coronation的音乐也是由简到繁、由弱增强。一位年轻法老的加冕,犹如投胎重生。而裸体的Akhnaten宛若童子,脆弱,却被命运往前推。
第三场的标题叫The Window of Appearances。整个剧的舞美用了很多方形框架图案,无论是舞台基础构建的“脚手架”,或是一个上下移动的简单的白框(看到那个白框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National Geographic!),还有时而作为Akhnaten背后光芒所采用的荧光灯管组成的一个亮方框,那个亮方框就是所谓的The Window of Appearances。我看到歌剧第一幕第三场结束的时候,Akhnaten、Nefertiti以及Queen Tye三人站在那个荧光灯组成方框里,终于意识到 – 不就是“同框”吗?的确,后来看了网上的一个解释说,这就是类似皇室向民众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或者平台。很直接的翻译。
第三场中假声男高音Costanzo饰演的Akhnaten终于开嗓。这样的音色选择,连我这个不懂歌剧的人,也觉得契合了神秘的人物形象和那种对太阳崇拜的神圣。第三幕结尾的Hymn (to the sun) 是我全场最喜欢的一段,也貌似是唯一一段使用英语的唱段。其他都是用了奇怪的希伯来语,阿卡德语,古埃及语,大多观众听来都是咦咦啊啊。另外一场Akhnaten和Nefertiti的二重唱用的却是某种奇怪的语言,两人红色的服装,互相交织,异域琴瑟的神秘。
幸好有了一位说英语旁白者。这位旁白者是整场歌剧中第一位开说的。他光头、长袍、气宇不凡。他每一幕都有一段旁白,戏份很重。到最后一幕,旁白者也化身为一位类似考古教授来介绍了Amarna考古现场。我一直以为此人的身份是祭祀,因为古埃及祭祀身份高贵,是与神的对话者。而第一幕结束后看了节目册,发现那人原来是Akhnaten的父亲,作为灵魂回到现场向观众解释发生的一切。这和第一幕中他的木乃伊被考古者发现,观察,以及他的心脏审判(心脏和羽毛一起称重)所呼应。若是心脏和羽毛一样重或更轻,那么就会有进入得以永生。
而真正的祭祀却是穿着欧洲古着的那位。燕尾服、高礼帽、礼帽上还镶着一个骷髅头。这样的穿越在这版剧中还有很多,无论是服装或是情节。第一幕第一场中的;而后出现的Queen Tye是一身维多利亚时期宫廷,头上羽毛顶着一面镜子;General Horemhab打扮好似非洲某国独裁者;而最后一幕更是出现了身着猎装或白大褂们的的。这样设定符合剧情转变,也承托了格拉斯混合着现代特征不断重复的乐句和时而变换的节奏。当然也可以想得远一点。这样的古代-现代设定,映射了那个即使在现代也不变的话题 – 磨灭与发掘、统治与变革、多神论与一神论?似乎第一幕和最后一幕的舞台构建 – 铁管脚手架也在暗示着同样的主题。第一幕和最后一幕的舞台构建都是为三层,而第二幕却不是,是否代表着三段历史中只有第二段是一神,且社会框架也不同于第一和第三段历史?
再说到Met这版的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亮点:杂耍! 从第一幕开始,就有一群身穿紧身衣的杂耍者,独自或互相抛接白色小球,第二幕是棍棒,第三幕又回到白色球,只是体积更大。把古埃及法老题材的歌剧和球球杂耍相配,的确大胆,而节目弹伤却有理有据地提到某种神奇的巧合:在 Beni Hasan墓葬群里的一幅壁画上描绘了三位杂耍抛掷球球的女子,这是有史以来第一幅记录杂耍的图像!而真正的编舞灵感应该是来自格拉斯的那一遍又一遍貌似重复但时而变化组合的乐句和节奏,正如球球在杂耍者手中不停地上下翻滚,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同时,从舞美来看,白色杂耍球是和谐与耀眼的太阳,却反差于舞台上第一幕和第三幕的方形构架。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幸好是用了白色的物体,并没有重叠与第一第三幕中服饰的华美,对整体听觉也并无累赘感 – 毕竟五官都是联动的,大脑注意力却有限。
这又带来了另外两个感想。我一直认为所谓的“简约主义”只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构架。而在这构建之下,可以是繁复的甚至是眼花缭乱的,无论是纵观这版的整体效果,或只是讨论到格拉斯的音乐本身,在所谓的“简约主义”构架之下有了空间和可能性去填充或者混搭,这即使在室内装饰中也同样适用。而版歌剧,编舞部分、舞美部分、服装部分对于所谓“简约主义”歌剧的填充,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随之,即使从没有听过格拉斯这部歌剧或者从没有听过看过任何歌剧的人,都可以无障碍欣赏,或者至少可以觉得“好看”。“好看”使得歌剧可能成为了准入门槛最低、受众最广的一种严肃艺术形式。这,我估计指日可待了。
7月 萨尔茨堡音乐节
SWR Symphonieorchestra & Teodor Currentzis
大多心愿实现的过程都是折腾自己。当快乐到顶点却是换来身心疲惫。
维也纳飞一小时到萨尔茨堡,坐的是左右各两排的“大型”螺旋桨飞机,维也纳机场起飞到半空,看过Lauda Motor的屋顶,我终于舒一口气 – 一定能赶上第一场音乐会。
不清楚这个Lauda Motor是否和Niki Lauda的飞机公司有关,但Niki Lauda的确生于维也纳确是祖籍萨尔茨堡。赛车史上戴着“生梨罩子”参加比赛的不多,Hakkinen之前就是Lauda了,Senna撞死,车王自己滑雪作瘫。
螺旋桨飞机到萨尔茨堡,没有接廊桥,看着萨尔茨堡机场也不会有廊桥 – 远远小于越南二三线城市归仁的机场。一个平坦小航站楼,三条行李带,没了。 哦,芬兰罗瓦涅米机场两条,还要小。
当然没有廊桥,旅行者们依次走下舷梯,走向接驳车,可是发现,只是我和少数几个旅客上了接驳车,大多数旅客竟然站在车外,望着自己的行李从机舱里卸下,并取走手提行李。原来“大型”螺旋桨飞机的行李架容不下大多数的18寸拉杆箱,只能寄存行李舱。
赶到酒店,冲澡换一身行头,就奔向Grosses Festspielhaus,那里上演Teodor Currentzis指挥SWR的肖斯塔科维奇《C大调第七交响曲 – 列宁格勒》。
惯例是身着黑色紧身裤宽松衫的Currentzis在舞台上的背影,就好像一只獾,他的高度是来自脖子的长度,而削肩细腰,指挥时时常往前倾,更强化了他獾的形象。
电影The Favourite,里面有一句台词是:You look like a badger,在电影里,Queen Anne被Lady Sarah指责为獾是因为烟熏而上翘的眼影。萨尔茨堡的Grosses Festspielhaus里有好多类似眼妆的女士们,穿着晚礼服,踏着高跟鞋。而男士们清一色的衬衫西服。走到今天才一睹欧洲音乐会遗风,瑞典波罗的海音乐节王室共存一hall的隆重,也不及如此。萨尔茨堡音乐节的着装要求是:elegant evening attire。
Currentzis可能因为他的高度,并不需要指挥棒,反正捷杰耶夫已经是牙签男,而某指挥参与制作的App中提到指挥棒的作用是:扩大身体的动作,可以让乐队看得清晰。Currentzis可能想利用乐队乐手站起来演奏的高度,去强化声音的层次感和强度,这也不算是什么新鲜做法。例如马勒《第一交响曲》里要求的圆号上扬,前年Eliot Gardiner同BR在演舒曼《第二交响曲》最后一章弦乐部全体起立演奏,的确是有不同的声音效果产生。这位指挥的另一个做法则是让某些低音乐器表现得更明显,比如钢琴和低音提琴的声音在整个乐队平衡里是加强了。所以,在第一乐章的进行曲段落,整个乐队加入演奏开始,全体起立,第二排的小提琴妹子已经开始扭动得好似金发陈美,声音变得无比的夸张,从四面八方冲到音乐厅的各个角落,而我希望我有一对兔子耳朵,才能容下所有涌过来的声响。反正观众听得很嗨,边上那对还乐到了抖脚。如法炮制的第四乐章结尾段落,更是恨不得把屋顶掀翻。所以Currentzis想说他的那些爆棚般的柴六和马六,都不是依赖于Sony音效师的后期处理,他想表明现场也能做到如此。
的确,他已经让SWR的弹奏方式趋同于MusicAeterna,所有的节奏第一拍超强,也就像说话的吃重音很重。而段落之间的强弱也被拉大。第一乐章的开头部分弦乐和定音鼓(甚至能感到地板在震动),进行曲段落从开头小军鼓部分,木管,铜管和弦乐、第四乐章开头部分,都有很不错的效果。可惜,一旦到了整个乐队都需要参与的高潮乐段,例如前面提到的进行曲段落后半部分,就完全没有了层次只是嘈杂。
无所谓,满堂观众都很开心,全体起立鼓掌,指挥被唤出来谢幕几次。SWR的弦乐齐整度提升很多,而乐手也好似热血演奏. 不好吗?这不就是古典乐整个业界想看到的双赢?
我感觉在第二乐章的时候,掐了自己的大腿,可能是由于第一乐章结尾处那种sacrifice of the war的死寂,更是因为在过去的21个小时中,我只睡了3小时。
两场演出:Medeamaterial 以及 Kraanerg
28日晚Dusapin的Medeamaterial和29日晚Xenakis的Kraanerg都在萨尔茨堡大学教堂里演出。一座巴洛克式样的建筑,白色的墙面,立柱,穹顶,祭坛上方的圣母像也是白色,背后点缀着金色的圣光,而七十一个小天使飞翔在圣母四周。1709年建成的教堂却上演了两部现代作品。
Dusapin的Medeamaterial开场没多久,一位女高音饰演的Medea没唱几句就飙到高音B。
她问自己:“你是如何活在自己躯干的残垣碎片中?”
这个高音直达五十八米穹顶,听着更为尖锐,歇斯底里。
爱、背叛、报复。Medea被爱神之箭射中爱上Jason,但后者却移情别恋。一段很长很长的独白中,Medea和背后的合唱,成为了“我”和“分灵”回答所有的控诉。
“我为你杀戮,为你生养
你的贱人,你的妓女
是你成功的阶梯
溅洒着泥污和死人的血迹。”
“请把我的结婚礼服作为你新娘的礼物
你的新欢犹如穿上我的皮肤
让我如此地接近你
而你的爱是如此地远离我
去参加你的婚礼吧Jason
我会把你的新娘变成婚礼上的火把
好好看下这盛大场面!”
歌词针针见血,一直飘在高音G上的复仇控诉段落在这周遭的巴洛克教堂环境下显得有几分诡异,所有的圣洁也许都有癫狂的成份存在。
我听Xenakis的Kraanerg录音,没有熬过一个小时就听不下去。但这部作品的现场演出置于教堂环境中,乐队和四轨录音(tape)的交替演奏,却产生了很独特的效果。
一来,现场乐队的声音,因为教堂四周声效环境而产生回声,这样的延时,使预先录制的录音和乐队的声音接续得非常好。有些段落之间的休止时间可以听清乐器的声音结束紧接着回声响起蔓延和终了。非常有趣的声音体验。
再者,预先录制的声音 – 低音部分,也就是作曲委约方要求的“要能显示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一流的音响系统的电子合成打击乐声响”,在教堂里听,就好似沉重的底下石棺盖被慢慢推开。而高音部分 – 弦乐的声音,则听似圣母像背后金色的圣光,尖刺般地放射出去。声音时而快速,好似腾挪的鞋底摩擦教堂的大理石地面,时而缓慢,灰黑的雾状形体在空旷的空间中盘旋,哈波迷都知道的Dementor?
可惜这场演到三分之二处,视野所及范围已经有五位观众离场。而到快结束时,也就是那两段长Tape段落之间,背后有位衣着正统的老妇,竟然笑出了声。
Xenakis在这部作品完成后,谱子上写了一段note:
“In barely three generations, the population of the globe will have passed 24 billion. 80% will be aged under 25. The result will be fantastic transformations in every domain. A biological struggle between generations unfurling all over the planet, destroying existing political, social, urban, scientific, artistic and ideological frameworks on a scale never before attempted by humanity, and unforeseeable. This extraordinary multiplication of conflict is prefigured by the current youth movements throughout the world.”
这个作品的理念,本来就是冲突和融合:现场和预录,传统与革新,现在与过去,现在与可预期而不可见的将来。而这些,使两部现代作品在一个巴洛克式样的天主教堂中被演绎有了更深层的意义 – fantastic transformation and extraordinary multiplication of conflict.
那位衣着正统的老妇请您继续笑,您的子孙可能会把《春之祭》作为古典入门,还可能会觉得Xenakis更带劲儿。
番外篇 – 追寻马勒作曲小屋
马勒在奥地利有两处作曲小屋,一处在Attersee,另一处在Maiernigg。前者离开萨尔斯堡只有2.5小时的路程 – 如果路上公交转接顺利的话。
第一程:
萨尔茨堡坐火车去弗克拉布鲁克(Vöcklabruck),四十分钟的车程,凡是往维也纳/林茨方向的都可以,没有任何选择问题。弗克拉布鲁克火车站是一座三个月台的小火车站,出门就是公交车站。按照google,要坐公车561到阿特湖畔舍夫灵转562。
第二程
561到了阿特湖畔舍夫灵(这个名字 – 有没有很像阿特湖畔失灵?)车站也在一座有一个月台的微型火车站边上。561的司机师傅带着我看了车站信息显示屏。
“啊,你就坐13:16分的562,就在这里等!”
太好了,还有40多分钟,我才不坐等。这里就是阿特湖(Attersee) 的一端,按照国内的说法,已经进入景区。若是自驾或者骑自行车的话,从这里开始环湖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人在湖边的草坪上一坐,看看天鹅,吃个热狗或冰淇淋,奥地利最惬意的夏天不过如此。
差不多到点走回到车站,还没见车来。一看显示屏,原来13:16分的562被划上了一道悲惨的横线,显示已经开走!奥地利乡下难道有隐形公交车吗??!!而下一班车在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来。看了Uber – 没有。看了出租 – 也没有。跑到对面的纪念品小店,想问老板可否帮忙叫车。没想到佛系的纪念品店老板说:
“错过了就再等等呗,上面那位这样安排,总是有原因的。可能你会遇到些事,也可能会遇到你的另一位。”
好吧,那么就等呗,顺便把午饭先解决了。
小店边上有一家湖景烤鸡店Hendl & Grill, 很简单的菜单:半只烤鸡,一只烤鸡,半只/一只烤鸡加薯条,貌似没有其他Grill,还有若干啤酒饮料。而店主十分骄傲于他的烤鸡,还专门摆盘供拍照。
第三程
吃完烤鸡薯条,562终于来了 – 这次没有隐形。
上车,坐到Seefeld/Attersee Gh Föttinger站下车。但这程若没有目的地或者是时间不限的话,可以一路随时下车观景,毕竟这车是沿Attersee行驶,简直就是观光车。目的地的站名:所谓的Seefeld就是Lake Field的意思,后半段Gh Föttinger也就是阿特湖夫亭格酒店。这是个重要的地点 – 若是在玩密室游戏的话,那么这里就是解锁关键。
到达后,进入营地,对的,一个露营地。阿特湖夫亭格酒店的边上有个露营地指示牌,沿着入口往里面走,满眼被卸了轮胎的房车(不知道为何?)、帐篷、以及挂在晾衣绳上的洗晒衣物。没有拍太多照片,因为怕别人以为我偷窥。朝着湖的方向走直走,左边是一深色的屋子 – 冲凉和厕所,右边一栋白色小屋,那就是马勒的作曲小屋。
房子的整体,标准得好像强手棋里的地产棋子,或者小朋友常画的那种山野间的房子 – 斜坡顶,四方墙体,三面窗户,一面门。只是小朋友不会在屋顶上加两个铁尖顶。从帐篷堆望去,白色的墙体未有任何污迹,好似长期有人打理,而背后的湖水湛蓝,屋子背后还露出了两张白色的沙滩椅,以及一顶红色的可口可乐广告伞。
想象太阳底下的另一个世界里,马勒拿一罐子可乐,坐在沙滩椅子上,看着湖景晒太阳。或是望见有个游客过来,拄着登山杖站起身,走到游客跟前想拉着聊天,说到激动处,还跺脚,敲登山杖。
我走近小屋,看见门上着大锁。从玻璃窗望去,一架钢琴,和另一扇窗后的湖景。湖里还有几人在游泳,还有三五游客正在屋后晒着。想必1893到1896年,这里的夏天应该没有那么喧闹。坐在这架钢琴后面看着湖,从晨光初露到日落余晖,可能都会有人游泳(说是马勒游泳骑自行车登山都很不错)多数时候他和自己的琴声、屋外湖水荡漾、和水鸟的鸣叫作伴。
既然小屋不开门,我转悠几圈后就准备走人。走之前去了次那个冲凉房和洗手间,但鬼使神差,出来后想再去小屋看一眼。
没想到靠近的时候听到了音乐声,马勒的《第三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无疑!不会是幻听吧?他的确在这里写了第三,靠近时窗户中看到里面有人,而别人是怎么推开门去的?正在屋外徘徊疑惑,屋里的一女子打开门问我是否要进来?
“当然咯,我都在屋外摸墙几圈了!”
那位女子手中拿着钥匙,起初我还以为她是管理员。
音乐原来是来自屋里的音响,估计有人来了就自动播放了?墙上贴着生平简介,小屋的故事,《第二交响曲》及《第三交响曲》的一些创作背景等。而钢琴占了小屋绝大部分的空间,使得在屋里的三个人,只能挨个儿转悠着看墙上的介绍文字。其中一位倒也自然,拿起相机,一屁股坐在了琴凳上开始拍照,琴凳被压的吱嘎吱嘎响。
后来才知道那位手持钥匙的女子不是管理员。
“钥匙哪里来的?”
“就在门口那个阿特湖夫亭格酒店前台拿的啊。”
果然如此简单,好似被安排。若是我坐上了那辆13:16分的562,说不定也就等不到这位手持钥匙的女子了,那么我也进不了小屋了。
从马勒小屋露营地出来后,还特意去了入口处的阿特湖夫亭格酒店,问了前台确认是否可以拿钥匙,还在那里买了些貌似没有人买的纪念品。前台服务员找纪念品柜子的钥匙找了老半天,还是我帮她找到了 – 就插在玻璃橱门上。难道我还要再来?
回程一切顺利,公车准时,562和561竟然变成了一辆车 – 司机师傅让我别下车,等着,他自己休息了一会儿,车牌一变,什么都解决了。好神奇。
两天后,听了赫伯特·布隆斯泰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竖琴开场四声铿锵,而大提琴音脉搏虽然虚弱但还坚韧。九十二岁的老爷子还是站立执棒指完全场,我没有听到任何生命末了的憔悴和哀叹,而是释然。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