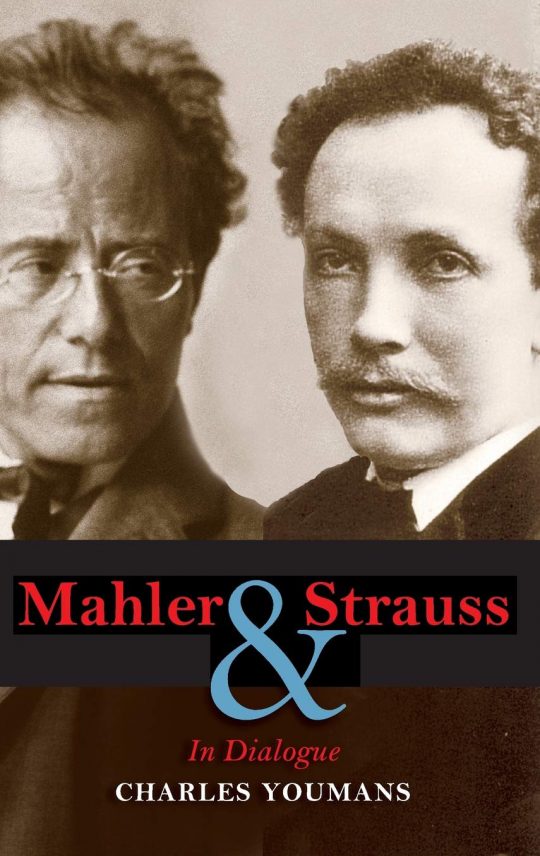作为反讽家的马勒和理查·施特劳斯
理查德·尤曼斯《马勒与施特劳斯的对话》(2016)第11章“作为反讽家”
Richard Youmans, Mahler and Strauss in Dialogue (2016), Chapter 11 “Ironists”
译|杨宁
即便是马勒和施特劳斯的路人粉也知道,他们的音乐,表象和实际的意思并不一致。奥赫斯(Ochs)示爱的圆舞曲激发不了热情;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多蠢,那这些曲子自己知道。《第九交响曲》“喧嚣而尖刻”的回旋-滑稽曲(Rondo-Burleske)中狂醉的扭曲所搬演的是“对赋格风格偶像破坏式的戏仿”。《家庭交响曲》的浮夸风格自显荒诞,且每处相似的大高潮皆是如此。而没有比《第五交响曲》末尾喧闹的特写让布鲁克纳显得更不布鲁克纳的了。[1]当我们对这种情况越来越敏锐时,例子也大大增加;精准而富有表现力地使用了某种音乐风格,却用来传达其反面含义——可以说,这两位作曲家的大型作品中,很难找到一部不是这样的。
此类时刻数量之大,已非批评家所能梳理,马勒尤是如此。朱利安·约翰逊(Julian Johnson)考察了逐渐细致的分类法,从罗伯特·萨缪尔(Robert Samuel)“对(以扭曲为目的)的戏仿和(以对立为目的)的反讽的有用区分”,到阿兰·勒杜克(Alain Leduc)对反讽的三种分类(“戏仿式”“批判式”和“悲剧式”),到斯蒂芬·E. 海夫灵的六大类(略)。最终,约翰逊理智地总结道,也许每部作品都自成一类:“我们越接近每一首歌曲或每一个乐章,明确的分类就越是让位于每一个个案的独特语气。”
特别是,在比较研究的语境中,后退一步是明智的。和他们所有的德奥先辈相比,马勒和施特劳斯更多地对他们自己音乐的严肃性提出疑问,或者更宽泛地说,要点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figurative meaning)的区别。马勒在1896年的一封写给马克斯·马沙尔克(Max Marschalk)的信中谈及《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明确地指向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反讽。这个乐章是早期作品中最为马勒式的时刻,作曲家称其“在亚里士多德‘反语’(eironeia)的意义上是反讽的”。这是什么意思?马勒援引自己所受的古典学教育,在此处引述了哲学家梅丽莎·莱恩(Melissa Lane)所说的“亚里士多德试图给eironeia的意义设限并固定下来,使之适用于修辞学中的一个技术性目的”。亚里士多德强行挪用了苏格拉底的一个多变的概念,把它的意思限定为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的对立。相似地,马勒也试图利用公开的谎言所具有的力量。例如,保罗·贝克(Paul Bekker)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这个乐章的:作品意在传达“伴随着毁灭性情感事件的那种感觉”,然而“这个事件没有用焦灼而激烈的语言,而是用一种显然无动于衷、不动声色的再现来表达的”,而这“加强了这一印象所内在的压迫感”。自然,马勒也受到浪漫主义先辈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也有——如杰里米·巴尔汉(Jeremy Barham)指出——间接影响,如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的“把严肃和幽默的概念过程(conceptual process)相结合的浪漫-反讽倾向”。但最终,他的根本目的直截了当:使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以带上相反意味这一点得到确立。
这就产生麻烦了,因为逐渐精准的方法有一种效果,就是可能的意思成倍增加。施特劳斯和他的作品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施特劳斯年轻时并不打算成为反讽家;他少年时期都在追求在技术上完整地掌握19世纪的所有风格(甚至包括18世纪的,比如莫扎特的风格)。他学作曲是通过模仿,结果就是他能轻易地模仿他人,而这就教会他一点:可以站在一定的情感距离外来运用音乐的表情。换言之,音乐能够欺骗,而施特劳斯能轻而易举地进行角色扮演,这让他拥有众多的选项来实践那样的操弄。就情感的明确性而言,这些工具有力而时新;施特劳斯后来解释说,19世纪晚期音乐最鲜明的特点是它具有空前精确的表现力(expression)。此前的观众都不会这样细致地熟知那么大范围的“风格-情感”关联,一个有真正技巧的作曲家能够利用这样的表情符号(expressive signs),因其可靠性让人非常笃定。特别是,通过瓦格纳,音乐实现了其宿命,“从复制模糊而一般的联想进步到表达越来越精确、独特而紧密关联的概念群”。这也意味着,和之前相比,表情(expression)越来越成为技术层面的一种功能,至少是在观众能够正确地回应的时候(而20世纪30、40年代的好莱坞经典电影音乐中所延续的那种后浪漫主义风格,其强大的力量证明了这种表达机制的韧性)。对施特劳斯这样技巧强大、幽默感过人的作曲家来说,把这种包容性用于操弄的目的,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步。
施特劳斯成熟期早期最经典的音乐反讽范例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背后世界论者”[2](Von den Hinterweltlern)一段那华美的降A大调赞歌。如果施特劳斯私藏尼采原著的页边笔记是一个精确的指示,那这本书里,除“康复者”(Der Genesende)外,当属这节最得其心。(“康复者”是这首音诗中段崩溃与康复这一标题内容的来源。)施特劳斯把“背后世界论者”分成四段,如下:
那时,我觉得世界是一位神的梦和诗;是在一位不满之神的眼前飘荡的彩色的烟。
从前我就是这样像一切背后世界论者,驰骋幻想于世人的彼岸。这就是世人的彼岸的真相吗?
啊,我的弟兄们,我以前创造的这个神,乃是人的制造物,人的幻想,像所有的神祇一样。
这个神是人,只不过是人和我的可怜的一段:这个幽灵,是从我的灰和烈火中出来的,确实如此!他不是从彼岸来的。我的弟兄们,宁可倾听健康的肉体的声音,那是更诚实、更纯粹的声音。
在以著名的C大调大自然景象开篇之后,施特劳斯此刻直接转向大自然的极端对立面:形而上的希望(metaphysical hope)。没有听者会怀疑施特劳斯对尼采的认同姿态,于是,只需对这一段的哲学语境有最基本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施特劳斯意在制造一个音乐谎言,一个会被拒斥的“梦与虚构”,而被选择的是“健康的肉体的声音”。作曲家此处确实编织出一个美好的梦境(第35小节标注“虔诚地”),用的是他习惯于表现神秘的、具有柔和神性的降A大调,还有丰盈的弦乐织体、虔诚至感伤的三度,以及支撑着狂喜的终止式(第66小节)的漫长属持续音——正经、美好到几乎不真实。积聚的雾气在短小却有耐心的尾声中渐渐消散,我们回到现实,回到一种明确的不安感。
施特劳斯一定觉得这段音乐的批判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为这种形而上幻想——这是驱动着尼采那创造性的智性创作的最重要因素——绘制了美丽诱人的形象。但是,期待听众也能轻松且没有抗拒地掌握这一暗示,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当然,同行之中有人认识到这段音乐是对宗教之空洞承诺的戏仿,是对一个不存在的领域的美丽描绘,是令人无法自拔、却意味着冷酷幻象之现实的温情。然而,以目前所知,施特劳斯当时的批评家里,没有人明确地谈到这一段的反讽特质。就好像,音乐的狂喜——以坚实的技术实现的一种功能——被呈现得太可信了,听者被甩下了作品的主要哲学论点。听者若没有认识到自然的、尘世的、反形而上的C大调和降A大调幻象之间的对比,就不能希望他们跟得上对“人类克服理想主义(idealism)的斗争”这一主题的更复杂精巧的处理。因此,施特劳斯在意义上最个人化的音诗必然坠入无名和混乱,他由此转到对观众要求不那么高的几个方向。
马勒的第一次公然的交响反讽实验也遭遇同样的困惑反应,原因却是相反的。所有观看《第一交响曲》早期演出的人都将第三乐章视为作品中最不寻常、最独特、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相似地,听众立刻把《马丁兄弟》这首歌(中文语境中即“两只老虎”的旋律——译注)的怪异扭曲视为某种反讽,有一丝悲剧的意味,但除此之外便令人捉摸不清。维也纳评论家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他对马勒经历了从热忱支持到残酷反对再回来的过程——在1900年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称,这部作品的主要障碍在于代际差异。视马勒为年轻作曲家(即便他已经40岁了)的老观众对讽刺毫无耐心,因为讽刺让感觉(feeling)和智性(intellect)产生了一种非自然的关系。“他们要的不是对感觉的戏仿——因为那总是心与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是纯粹的智的游戏(机智 [wit])或纯粹的心的游戏(幽默 [humor])。”对这些老观众而言,头脑是反讽所具有的距离感的处所;它在悲剧这一严肃语境中没有位置,因为它威胁到悲剧感所必需的情感连接。而年轻一代音乐会观众则已经开始怀疑情感是否真诚;马勒的音乐是只对他们言说的,因为“只有他们能享受对神圣情感的戏仿和扭曲”。(汉斯立克证实,至少在这场演出里,观众中的年轻人叫好了,而老一代始终感到困惑。)在假设任何真诚表达,无论是不是悲剧,都无效的现代主义戏剧语境里,“享受”大概是“准确诠释”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悲剧成了新的喜剧,扭曲、甚至一种新的滑稽被用来重新激起已死的感情。
这个乐章里的G大调田园诗(第83小节)是一个证明了这条法则的例外。格拉夫正确地判断道,在这里,“真的、完美的感情浮现了一会儿”,是一个被“漫画”所环绕的绿洲。音乐毫无疑问是真情实感的,和施特劳斯的“背后世界论者”完全不同。施特劳斯采用诚实和深刻的调子来公布他自己的怀疑主义并以此表明立场,马勒则放纵于自己的第一个死亡幻想。如果这段音乐和其他的一样,即便对作曲家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可信,那它似乎其实是言其所是的,或者说是想要相信它所提出的。用布列兹的话,我们可以说,它位于“感伤与反讽、怀旧与批判的分界线上,而这条线有时是不可能清晰明确的。”反讽的距离感几乎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由扭曲的音乐技巧所带来的反思。泰奥多·赫尔姆(Theodor Helm)把这个时刻聆听为对“走向公然戏仿之前驱力”的打断:戏仿始于对《马丁兄弟》的扭曲,接着是那段明确标着“戏仿”(Parodie)的“具有匈牙利式表象”的旋律。罗伯特·希尔施费尔德(Robert Hirschfeld)同样觉得,在这部他讽刺地称为“交响曲面目的讽刺剧”和“对交响精神的戏仿”的作品中,这少数几个清晰“严肃”的时刻——包括终乐章里布鲁克纳式的降D大调旋律在内——是令人瞩目的例外。上述描述也同样可以应用于施特劳斯的降A大调烟雾和幻镜,但正如犀利却真诚的希尔施费尔德所指出的,马勒的“菩提树音乐”中没有任何一丝不诚实的东西。无论普通听众如何理解这两个高度严肃的表达,作曲家们自己很清楚批判性的反讽和愉快地沉浸于无用渴望之间的区别。
格拉夫继续抱怨说,马勒混淆了头脑与心灵——斗争制造出不纯粹,制造了“对感情的戏仿”而非真正的感情。在这方面,他引述了科西玛[3]对《唐璜》[4]的深具观察力且极为重要的反应。她同样认为智力与感情是不相容的,因此对这部作品独特的目的和力量感到憎恶。此处所谈的智性并不是对音乐过程的思考,如曲式、对位、展开等。这些东西可以在人的感知的背景中运作,对表达行为的作用相对被动。此处的智性,指的是让科西玛和格拉夫感到困扰的、对表达自身的批判性思考。马勒和施特劳斯以不同的方式——前者重在扭曲,后者重在以音作画——让人注意到情感表达,并对其可信性(authenticity)提出质疑。正如科西玛和格拉夫可能在马勒和施特劳斯之前就意识到的,这一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旦音乐不再默认是作曲家和听者之间的可信的情感连接,那浪漫主义表现机制的基本条件就不存在了。反讽是一种“一旦有便不可能没有”的姿态,换言之:一旦出现反讽,那些怀疑便不可控了。
既已走出无法撤回的一步,两位作曲家就都尝试构思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其中,对情感表达之表演的反思可被当作第二层情感沟通的来源。对施特劳斯来说,这个过程在两部音诗和一部歌剧中展开,即显然组成一对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英雄生涯》(Ein Heldenleben)和全面讽刺的“非歌剧”(non-opera,施特劳斯称为Nichtoper)《火荒》(Feuersnot)。在第一首音诗里,遭科西玛痛批的用音作画的智性被彻底释放,只有一个时刻强调了另一个维度,即杜尔西内娅(Dulcinea)激发的高等骑士精神的精致、美好的幻象(第332-369小节,升F大调)。仅在这一个时刻,里特尔受豪泽格尔启发的“表情”(Ausdruck)[5]被放在聚光灯下,供我们欣赏和分析、思考。正如在《查拉图斯特拉》里,这里也有明显的离间效果,因为这是其他人的视象。然而,因为和里特尔的私人关系——这是隐而不宣的微妙之处——对堂吉诃德命运的无奈沉思仍然保持着一些感伤的力量。要是写在十年之后,这音乐完全可以是写马勒的。悲苦的展开并不令人生疑,但其批判性依然存在。
如果《堂吉诃德》代表了里特尔和马勒也都有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视角(至少大体而言),那《英雄生涯》就把镜头对准了作曲家自己的选择,并以令人释怀的诚恳评估了他自己的肤浅。就其超过半小时的长度而言,作品的曲式规划简单得令人吃惊,在音乐和标题性两方面皆然:音乐上,它是一个直白、普通但臃肿的奏鸣曲式;标题性方面,它由数量不多、极为清晰的几个事件连成。在其他所有作品中,施特劳斯都没有这么明确地避免模棱两可。但即便这首音诗削弱了英雄性这个概念——主角和敌人就在此时、此地打着平凡的战斗(即作曲家和乐评人之间),它对它的目标施以讽刺技,却带着致命的严肃性,而不是幽默。这一选择反映出敌人的本质。施特劳斯写道,在这部作品中,他所与之斗争的,除了外部的敌人,还有“内在的敌人”:“怀疑、嫌恶”——这是尼采式的标语,指的是在一个对音乐形而上学上瘾的文化中拒斥理想主义时所产生的不适。用艺术的手法描绘这种冲突,需要双重的戏剧性反讽;在倒数第二段,我们看着作曲家看着他自己,接着,我们见证他逐渐意识到,他的朝奥尼采式反浪漫主义的进化只会让他疏离,给他带来艺术上的孤独。由此,他走向避世,遁入一个私人领域,他在其中成为他的创作的唯一标准。
在人生尽头,施特劳斯提供了一份对自己艺术人格的解读,虽只是个短小的片段,但依然颇有启发。他在其中特别指出,反讽是在从《贡特拉姆》(Guntram)到《火荒》的一系列作品中出现的。歌剧始终是他最重视的体裁,但这种最具特色的倾向却是在一部“非歌剧”中浮现到他的自我意识前端的。“在《火荒》里,那刻意的嘲弄、反讽的语调……代表着我个人的创新。”当施特劳斯从关于形而上学的辩论中回撤,并开始构建前路时,他意识到,对形而上客观性的批判也会波及主观性。他以批判形而上学为根本,拒绝稳定的客观性框架,作品由此聚焦于对主观性的一种新的解读。批评家完全没看到这一点,85岁的作曲家哀叹道:“他们为什么没看见我作品中的新意:也就是 [作品背后的] 个体如何在作品中显现,正如仅见于贝多芬的那样?”但批评家没看到这一点是因为施特劳斯此时呈现给他们的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没有稳定身份的主体——一种不系缚于任何客体的、随机应变到夸张恣意的个性。如果如他所说,“让我的戏剧作品不同于”与他同期的“典型歌剧、弥撒、变奏的,恰是”“自白”(confession)这一因素,那么,这份自白来自一个只靠反讽来自我呈现的主体:他戴着许多面具,因为他除了面具就没有别的了。
莫尔腾·克里斯蒂安森(Morten Kristiansen)将《火荒》在风格上的异质性诠释为世纪末“风格艺术”(Stilkunst)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异质性把主体性的后形而上碎片化提升到了成为一种艺术原则的高度。施特劳斯拥抱“当时文化生活的主流元素,即多元性和碎片化”,创作了一部既戏仿、又赞美了慕尼黑音乐生活之全景的歌剧——从瓦格纳到巴伐利亚民歌,从古代风格到轻歌剧,从圆舞曲到他自己的风格偏好,不一而足。通过万花筒般的并置,作曲家解放了听者对风格重心的感知,以风格为方式确证了自己的结论:音乐之存在并不是为了传达其自身以外的什么更深刻的现实。唯一比混合了竞相出现的各种风格——克里斯蒂安森把它们事无巨细地加以整理,特别是对瓦格纳的指涉——更令人困惑的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所有这些风格都不是作曲家自己“本真”的表达方式。以风格论,克里斯蒂安森正确地认为《火荒》是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发端的一份有力陈词(莱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曾在论及施特劳斯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作品中谈到这一方面)。但这种拼贴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客观美学”,而是拒绝参与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以及主观性。在他的第一部歌剧中,施特劳斯总结道,音乐和客观性——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现实”(reality)——没有关系;在第二部歌剧中,他认识到,客观性的终结意味着主观性脱离了任何稳定的地基。随意性、去中心化现在已成了不可避免的思想现实。用艺术的话说,这就意味着哲学上唯一诚实的处理风格的方式就是反讽。《火荒》中有世纪之交时慕尼黑所能见到的几乎每一种音乐风格,但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是大大方方地、不带冷眼旁观的反讽迹象(要么戏仿,要么感伤化)来使用的。而这一点的重要性高于任何会被当作施特劳斯独特风格的东西。
似乎可以说,施特劳斯对自身的痴迷不亚于马勒,就算他完全放弃追求真心的自白。德累斯顿的音乐总监弗里茨·布什(Fritz Busch)说:“我无法、而且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成功解出施特劳斯之谜,也就是,尽管他有着最惊人的才华,但他不像其他艺术家,既没有被它充塞、也没有被它攫取,而只是像穿着一件外套,可以随时脱下。”而另一边,马勒则继续构建走向真实的自我。《第六交响曲》就是一例,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份直白的自传性预言,而是因为它让自我刻画远离反讽,就好像在触及如此私人的话题时,距离、怀疑、犹豫都没有位置。它和《第五交响曲》形成极端的反差:后者从悲剧走向诙谐,途经感人至深的告白(即“小柔板”),而这一告白成了疯癫但善意的伪巴洛克喧嚣的素材。阿尔玛对《第五交响曲》的反应一定让马勒伤透了心,她的话不仅呼应着对《第四交响曲》的轻率否定(“我觉得海顿做得更好”),更暗示说,马勒背叛了或至少忘记了他自己的一些基本元素。特别是,最后的圣咏段(她称为“无聊的赞美”)迫使她“让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本质和布鲁克纳极为不同”。玩弄布鲁克纳式的天主教正统,即便拿幽默的过度来掩饰,也强调出“他的存在中的裂隙,这道裂隙深到让他和自己产生了严重冲突”。因此,阿尔玛在这个乐章里读出的反讽是无意识的——马勒的音乐背叛了他,欢腾的表面揭示出黑暗的内在,至少在阿尔玛看来,此时此刻作曲家没有注意到它。
在他计划下一部交响曲时,这些评论显然影响了他。下一部作品中,他以悲剧替换乐观我,尝试进行更真实的自我评估。在《第六交响曲》中,马勒把自己当作英雄原型;受古典主义影响的谋篇和单一色调的悲剧基调把听者的注意力从局部转移到整体,确保没有人会误解这一份类似《英雄生涯》的自画像。但尽管有自传式的内容,马勒却和我们一起站在剧情之外,采用了戏剧性反讽的姿态;我们和他一起见证了英雄的倒塌,害怕那个我们预见到、但主人公却没有见到的命运会成真。对作曲家个人来说,维持那种反讽的分离最终却是不可能的。他好像真心“害怕这部交响曲的预言力”,以至到了要去掉终乐章里第三次锤击的程度(除迷信外无法解释)。在埃森首演的后台休息室里炙烤着他的就是这种恐惧,而这事可能是马勒和施特劳斯之间最大也最痛苦的一次误会。[6]对个人的这层意义解释了行板主题的感伤风格,贝克尔称它“几乎流行到反讽的程度”,试图令人感动地把作曲家从自己身上拯救出来。
施特劳斯竟会误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当然是不可信的。音乐的救赎企图通过对《帕西法尔》(Parsifal)的明确指涉而传达出来,这对一个瓦格纳指挥家来说再有力不过,并且在1906年时,他早已在长期的经历中理解了马勒的世界观。他不需要听到第一乐章中和阿尔玛有关的F大调主题;只要看到它的轮廓、配器、冲动的节奏和语境(即这是一幅音乐自画像中的元素),他就立刻能知道;甚至,他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主题和他在《英雄生涯》中对保琳的描绘所形成的对比而呵呵一笑。同样,施特劳斯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这部作品和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关系——这个主题的轮廓和作为一部交响曲所罕见采用的A小调就足够清楚了。施特劳斯在排练后的作为并不是因为他误解了作品和马勒对它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太理解了。他刻意表现出无情而不耐烦的一面,轻率地提到市长死了所以音乐要改一下,是为了让一个被自己的交响曲洗脑了的朋友回想起事情还有其他面向。施特劳斯似乎在说,用音乐来祭奠悲剧英雄的做法老套得不可救药,更不用说把自己当成主人公放在这样的仪式里。
1900年左右,两位作曲家的创作都出现了转折:施特劳斯义无反顾地从音诗转向歌剧,马勒从标题音乐转向“绝对”音乐(他本人语)。这显示出,他们在处理反讽方面转换了角色。马勒“魔号”交响曲的特色——大胆的音乐戏仿实验传到了施特劳斯手中,他在《火荒》、特别是《莎乐美》中证明,他能够对听众贩卖怪诞和扭曲而不会被打发为陌生和不协调。《莎乐美》中最恶名在外的时刻,尤其是面纱之舞及其后续,从《第二》和《第四交响曲》的谐谑曲中挪用了一种技法,即让不悦感、甚至一种眩晕感迫使听众出离,以要求他们做了保持距离的反思。(贝克尔用“魔鬼般的”一词来形容马勒音乐中的这种特质,把戏仿、反讽和挖苦合并成更大的类型:“不时怀有恶意,不时苦楚,很少且只在转瞬即逝的时刻不是有意的”。)但在施特劳斯手中,这些工具直截了当地传达到了听众那里;马勒无法复制这一点,也无法理解,就像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施特劳斯的配器实验总是第一次就能成功。同样地,1900年之后,马勒开始远离讽刺,走向施特劳斯前三首音诗里的那种表现基调,对以贝多芬、柏辽兹和勃拉姆斯为校准的听众来说没有难度。甚至《第七交响曲》那喧闹的赞颂和缺乏修养也代表着一种对贝多芬兴高采烈的庆典模式的历史回顾。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场合的谈话里,都没有迹象表明,马勒是因为备受打击而选择这条路的。他急切地想被听到,被欣赏,并且到这时,他已经知道不加掩饰的反讽不会让他成功。
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关系鼓励了施特劳斯天然的倾向,让他用音乐风格来思考艺术的本质。确实,这种做法后来逐渐清晰起来,在《阿里阿德涅在拿索斯岛》(Ariadne auf Naxos)一剧的作曲家一角中达到顶峰。在这部歌剧的第二版(即最终版)中,施特劳斯对这个角色慎思精虑,恰好是因为他在内心里憎恶他。在作曲家与脚本作者的这段最为艰难的合作经历中,施特劳斯坚持要把作曲家设定为“穿裤角色”(即女扮男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体貌符号,以示要和一个宣扬“音乐是一门神圣的艺术”的艺术家保持距离。施特劳斯一生中仅有一次玩味了一下这样的说法,当时他把旋律灵感描述为“世界精神(World-Spirit)的无意识发言人”、“神性的最高赠礼”,以及“终极神秘的绝对启示”。对施特劳斯来说,这些都是例外的倾泻,(在同一篇文章里就)立刻从形而上世界被转引到自然世界。他说,他的人生经验告诉他,“人类的血液中有一些化学元素,它们在流经某些神经或和大脑某些部分产生接触时会引发精神和心理活动的最高程度的刺激,就此产生艺术杰作”。根据年迈而逐渐感伤的施特劳斯,甚至最高贵的精神表达也有其成因,隐藏于人类身体的物理现实之中。“大脑、神经、血液,哪个是最强制因素呢?”他反问道。
这样的想法,《阿里阿德涅》(1912年作,1916年修订)里的作曲家——一个不可救药的原型浪漫主义者——是想不到的。在一个明确非瓦格纳式的脚本和戏剧语境之内,这个角色操着理想主义的旧语言,其话语、其音乐都是如此(在后者中更为重要)。而现在,瓦格纳式的和声与管弦乐技法成了一次历史主义实验——漫游于西方经典、从各自语境中撷取着不同风格以构成戏仿拼贴的一部自知的现代作品——中的一个样本。莫扎特、舒伯特、贝利尼、唐尼采蒂、法国洛可可、即兴喜剧等等——西方经典的历史组成本身就是核心戏剧主题,其重要性不亚于作曲家的歌剧创作及其喜剧性的对手。但如果,像布莱恩·吉廉(Bryan Gilliam)所说,《阿里阿德涅》“打造了作曲家、演奏者和观众之间的新的关系”,那它这么做不是为戏仿而戏仿,而是使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明确看到这种新的关系。施特劳斯音乐中的反讽维度现在已经被多个戏仿的并置所限定,他比先前更强调、更要求观众思考音乐的力量以及他们对艺术的期待。我们把每一种元素均视为戏仿,在其中,风格的对位自身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它否定了浪漫主义音乐最鲜明的、也是作曲家这一角色所继续颂扬的直接性。因此,在《阿里阿德涅》之中,定义了施特劳斯的现代主义的,不再是他本人和他的音乐的距离,而是音乐——任何一种音乐——和它的听众之间所被强加的距离。
当年迈的施特劳斯在《随想曲》(Capriccio,1941)中再次回到这个模式时,他又一次(在另一个维也纳脚本作家克莱门斯·克劳斯 [Clemens Krauss] 的帮助下)创作了一部兼作美学沉思的音乐拼贴。在这部歌剧中,他带来了让《阿里阿德涅》成为音乐现代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常青范例的那种谦逊和轻巧的智慧。这部作品和《达奈之爱》(Der Liebe der Danae)的关系并非不像《阿里阿德涅》和《没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的关系——后一部的缘起都比前一部要早。《达奈》的存在否定了施特劳斯的说法——《没有影子的女人》是“最后一部浪漫主义歌剧”。这两部的瓦格纳风格都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它们都让置疑悬停了足够长的时间,让人沉浸于过往。因此,这部晚期作品回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微妙反讽:一种已死的风格得到如此有力的呈现,让人差一点就相信它了。但现在,批判性却被类似席勒感伤主义的东西给柔化了,好像充满悔意地瞥见什么美而不可复得的东西。整个创作晚期,因施特劳斯不断重新审视他年轻时的模式,都有这种情绪的证据。前文(第7和10章)已描述过这种策略中的自传性和互文性,此处我将关注它的反讽维度。施特劳斯的每一部晚期作品都显示出——也许是有意地——某些远离所用模式的迹象。在《变形》(Metamorphosen)中,音诗作者抛弃了他标志性的恶作剧式的音画法。他称为“活动一下手腕”的、受古典主义启发的作品则不像19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不再有延续一个鲜活传统的意图。而《四首最后的歌》尽管有着令人想到那位拜罗伊特大师的丰盈配器与和声,在其迷醉的抒情中却轻巧地飘离瓦格纳,而不是与他批判性地相交。因此,在回顾过去的自己时,施特劳斯为了把自己和每一个自己区分开,无法抗拒使用反讽,即便这么做让他无法发现一个最终的、稳定的个人身份。
施特劳斯在晚年把反讽用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的主体性碎片作为史学项目创作出来,把他当下的自我和之前所有的可能性相分离。而马勒则从自己的过去抽取一条线索,以其为基础,最后一次尝试寻得慰藉。吕克特诗《我已被世界遗弃》(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那静静的弃世反映了东方和叔本华的影响。这种姿态让马勒创作出一种永恒静态的音乐风格,即五声音阶和共性写作和声的复合体,其“消散以目标为导向的西方和声进程”的能力成就了他成熟世界观的音乐表达。《大地之歌》毫无疑问是对自我的寻找,这个自我并不把过去的尝试视为对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可能回答,而是视为失败。“如果我要再次找到回到我自己的路,那我必须臣服于孤独的恐怖,”他对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写道——他也许是音乐家中和他精神最相契合的了(另外还包括阿尔玛和纳塔莉·鲍尔-莱希纳 [Natalie Bauer-Lechner] )。这里,难处并非如他所说,是对死亡的害怕,而是与他人的疏离;它隐含在主观与客观那无法跨跃的鸿沟里——这是马勒整个艺术生涯最大的困扰。马勒并不觉得和自己切断了关系,我们甚至会觉得要真是那样,他反倒会松口气。相反,他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沟通,而这,对一个深信自己有能力操弄人类所知最有力的沟通艺术的艺术家来说,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情形。而正是这种不抱希望,才让他——如贝克尔所说——成了《第九交响曲》中间乐章那“黑暗力量和种种阴影的召唤者”。在那种悲伤的状态下,反讽能辨识出问题,达到批判性的目的,但它无法成为前进的道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不是其他原因的话——《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的结尾在我们听来是个人化的、积极的,却不是乐观的。乐观讲的是未来,而这几部作品中只有现在。
[1] 指马勒的《第五交响曲》。
[2] 章节标题和引文采用钱春绮译本。
[3] 李斯特之女,瓦格纳之妻。
[4] 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
[5] 亚历山大·里特尔(Alexander Ritter,1833-1896)是将施特劳斯引向“新日耳曼学派”的关键人物。弗里德里希·冯·豪泽格尔(Friedrich von Hausegger,1837-1899),音乐学家,著有《作为表情的音乐》(Die Musik als Ausdruck),主张音乐他律论。
[6] 首演前,马勒心神不宁,施特劳斯只非常不耐烦地说:“这人怎么了?”余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