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纪实:《太阳帝国》掠影(或称一则希望引起编辑关注的评论)
文|小河
出生于上海的英国作家J. G. 巴拉德(1930-2009)在离开中国近四十年后写下了他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记忆。文学化的一段历史以十几岁少年的视角道出,《太阳帝国》这部近四十年前的布克奖短名单小说是巴拉德与中国/上海最直接相关的一部作品,同名电影更广为人知。巴拉德其他作品的读者往往能在《太阳帝国》中找到他幻想/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可惜的是,《太阳帝国》中译本(2007,2010)已绝版多年,巴拉德的中译本目前仅有《混凝土岛》(2021)和《摩天楼》(2017)可见。(2009年的《撞车》同样绝版。)下面这篇文章一方面想和大家一起观察作者在《太阳帝国》中对历史与记忆的文学化——这仍是我们能浸入某段历史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遇到感兴趣的编辑,促成《太阳帝国》中译本的出版。本文对《太阳帝国》的引用均引自胡凌云译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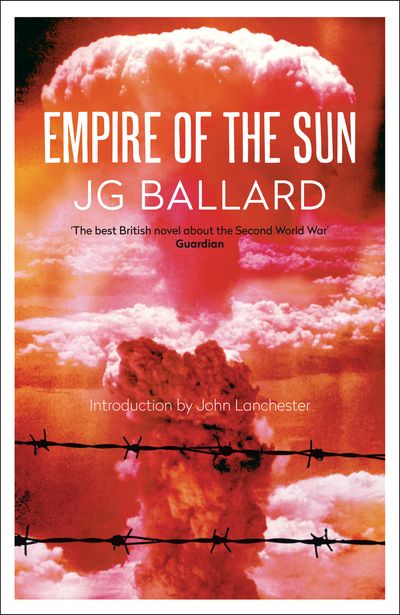
4th Estate, 2014
“我一直在想体育场的问题,小说里说蒋夫人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缘故下令修建,又说是混凝土建筑,不应该更像北边的市立体育场吗?”
“已经想过很多遍了。作者为了方便吧。”
“意思是作者为了行文方便,把体育场挪动了?”
当我的目的是写一篇希望编辑们能注意到这本书(并且考虑引进)的评论时,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前不久看这本书译稿,中途收到一份文档,《老上海地图》,“别沉迷于空想”。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地图。《太阳帝国》中的地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嵌入大脑深处,不管精确与否也能在头脑中绘出样貌。有一阵日日夜行,在上海路面上温习纸面看来的路名。巴拉德于1991年重访上海的纪录片《上海吉姆》也是那时看的,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少年吉姆走过九十年代上海街头“魔奇世界”大幅广告画前,背景音中巴拉德讲,他的作品讨论构成我们世界的虚构与现实。
《太阳帝国》因电影而知名,巴拉德也因这部小说有了更多读者。从中文读者的视角来看,这本书当然有很多可说。“二战”、盟国侨民集中营、殖民主义、Shanghailander的侨民生活,具体到细节也可以讲讲小说里提到的几条“越界筑路”。而在小说为我们重建的八九十年前的那个时空切片下,在这篇“评论”中我最想谈的是全书后半部分出现的那座“体育场”。
“夜幕降临一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南市西郊的一座足球场。这座混凝土场馆是蒋介石夫人下令修建的,当时希望中国能举办1940年奥运会。1937年日军入侵后占领了这座体育场,将它变成上海以南战区的军事总部。”(注:引自《太阳帝国》胡凌云译稿,下文未注明处亦同。)
《太阳帝国》中的体育场一开始吸引我的注意,是其虚构的特征无法与认知和记忆重叠。我试图将它与现实精确对应,但又发觉自己的行为早已超出虚构读者应有的心理活动。这背后是否隐含着我们应该如何读(历史)小说的一点线索?或者,钟情历史的读者如何从虚构中获取所需?
“吉姆盯着体育场坑洼的外墙。炸弹碎片削掉了部分白色石膏,原来宣扬国民党力量的汉字重见天日,咄咄逼人的口号悬挂在黑暗之中,就像战前上海中国电影院上方的那些展牌。”
体育场是吉姆离开龙华集中营之后的一个重要场所。这当然超越了搞清楚“体育场”究竟是不是“南市公共体育场”这一细节的意义。故事从集中营的封闭空间转移到体育场这样半开放的空间,连接其间的是陌生的道路。许久没有踏上,延伸到回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在土路上目标明确地向前走去,双眼盯住法租界公寓楼的黄色外墙,它们像海市蜃楼一样从运河和稻田中升起。”)熟悉的人物仍在体育场现身,以及熟悉的死亡。在这里物品并非错置,不过是寻常风景。
“吉姆的视线搜索了体育场北坡和西坡的看台。水泥土台上的座椅已被拆除,几段看台如今被用作露天仓库。几十个黑木柜子和桃花心木桌子的清漆依然完好,它们和数百把餐椅挤在一起,仿佛是家具仓库的阁楼。床头柜和衣柜、电冰箱和空调机堆成了一道朝天的斜坡。蒋夫人和委员长本来可以从中向各国运动员致意的巨大总统包厢如今挤满了轮盘赌桌、鸡尾酒柜和将华丽罩灯举过头顶的鎏金石膏仙女。一卷卷用油布匆忙包裹的波斯和土耳其地毯躺在水泥台阶上,其中滴出水来,仿佛是一堆腐烂的管道。”
“他们跟随褪色的标记线,不知道自己要去何方,仿佛他们在整场战争中幸存下来,只是为了在这座简陋的迷宫中死去。在体育场外,八月的阳光在稻田和运河的彻底寂静中显得更加强烈。荒废的大地上覆盖着一层白釉。这片田野是否曾被欧亚混血所说的原子弹的闪光灼伤?吉姆想起了野马式飞行员燃烧的尸体,还有那道充满了体育场、似乎给死人和活人都穿上了裹尸布的无声光芒。”
这些段落看起来纪实,但和纪实文学毫无关系。反而让人联想起来他真正的幻想故事。(安吉拉·卡特说《太阳帝国》表面上是“自然主义”,本质仍是想象。)小说家非常懂如何描述和操纵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是这样吗?巴拉德经常说他一直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和战争的小说。花了二十多年忘掉上海发生的事,之后,又花了差不多的时间回忆它们。回忆并不仅仅是记起来,而是为其增添细节,将其重新神话。
故事进展到“体育场”,无论是场景还是内外人物,看起来比前文的龙华集中营生活要超现实多了,似乎从踏出龙华的那一刻起,吉姆虽然“重获自由”,但进入了一个介于“可理解”与“不可理解”之间的现实。在2008年出版的巴拉德自传《生活的奇迹》(Miracles of Life)中,似乎可以捕捉到作者心态的变化。他提及集中营生活对他(十几岁的男孩)来说找到了某种自由。而1945年8月又是一个奇怪的权力过渡期,他们不能完全确认战争已经结束,这种感觉伴随他数月甚至数年。直到他写作自传的晚年,坐在扶手椅中打盹时,也能短暂地感受到那种不确定性。

电影《太阳帝国》,1987
在《生活的奇迹》中,巴拉德没有提起“体育场”。但他记录下来,现实中的他确实曾在走出集中营后一次次重返。有些侨民在战争结束几个月后还住在那里。龙华的气氛已经变了,他目睹了荒地上集中营侨民和当地农民激烈争夺B-29投下的物资。
“吉姆躺在一捆丝制降落伞上。他一直都明白,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景象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过于巨大的诱惑。自从他回到龙华集中营之后,那群英国人就一直在讯问他关于看台上被掠家具的情况。为了保证自己从指挥官办公室获得罐头和杂志供给,吉姆被迫用个人记忆添油加醋。如今,他的虚构已经占据了普莱斯的想象,要想回头已经晚了。”
“目睹这位死去的飞行员令吉姆感到麻木,他望着少年的膝盖渐渐滑入水中。他蹲在坡地上,翻阅着《生活》的纸页,努力把精力集中到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照片上。长久以来,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年轻飞行员身上,徒劳梦想着他们能一起飞走,将龙华、上海和战争永远留在身后。他需要这位飞行员来帮助他在战争中生存下来,作为他发明的想象中的孪生兄弟,一个他透过铁丝网观察的自己的复制品。如果这个日本人死了,他自己的一部分也死了。他以前没能领悟到千百万中国人生来便知的真相,那就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生不如死,假如另有想法,必然是自我欺骗。
吉姆听着虹桥和徐家汇的炮击,听着国民党侦察机盘旋的低鸣。小型武器的射击声穿过机场,这是贝西和匪徒们正在试图闯入体育场。死人们正在玩他们的危险游戏。”
战后,搬回安和寺路老家,巴拉德曾骑着新自行车数次重返龙华,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少年流连一段时光,还因为他并没有真的离开战争。《太阳帝国》用“体育场”这个空间作为某种缓冲区,同时展演战前战后和战时。这样的画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与巴拉德曾经的重返活动相似的感觉。他也由此复现了他当时的感受。“也许战争并未结束,或者是我们进入了一个介于中间状态的世界,在某种层面上它将延续数月乃至数年,融入下一场战争。”(《生活的奇迹》)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吉姆,早早觉察出旧帝国的没落。因此,不同于成年人对旧帝国的信心(战争很快会结束),少年的他们一直注目日本年轻飞行员,而现在日本年轻飞行员的死也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早在1944年,他们的目光就转移到了美军轰炸,先进的美国飞机也成了最新的青少年崇拜对象。
这是一个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英国少年眼中的上海和战争,当然还有别人眼中的上海和战争。茅盾的一部并不热门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开篇场景便是1937年7月7日城市北部的“市中心”市立体育场。作为一个重拾历史且熟悉上海的人,我在电子屏幕上翻看1937年发行的月刊《上海体育》,这是市立体育场的场刊,刊载有体育救国的文章和体育场职员名录与董事会会议记录。这份刊物发行了四期,与那一年的很多事一样貌似规规矩矩却戛然而止。等战后的市立体育场再次迎接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之时,修缮名目与迟迟不走的驻军让人得以一窥战争的痕迹。


战前的市立体育场
巴拉德以少年的视角捕捉到了旧帝国的没落以及旧帝国心态的某种延宕。集中营的英侨民仍沉浸于谈论英国的武器,而美国海员却从不吹嘘。虚构中吉姆提起父亲面对工厂工会的压力,现实中巴拉德父亲负责的纶昌纺织漂染印花公司在1939年面临了长达半年的、牵涉中英日多方的罢工(也有一位白俄保安卷入其中,典型的上海故事)。工人因要求加薪与需要发展组织的地下党联合,混杂着日占区酝酿的排英运动。罢工演变成多方的政治角力。因与日军冲突而死亡的纶昌雇员英国人廷克勒(Tinkler),后来成了毕可思Empire Made Me(《帝国造就了我》)一书的主角。他的死,注解着旧帝国影响下的上海业已消失,而正因为仍回荡在记忆中的光辉,才催生了这起徒劳且致命的事件。这是租界形势岌岌可危之时,很快“越界筑路”的警权也要移交给“特别市政府”了。

罢工伊始,H.M.S. Decoy英水兵登陆浦东,看守纶昌,这张照片是1939年5月的H.M.S. Decoy

1939年5月,几天后,英军撤退,日军在纶昌厂外

与上图同时的纶昌布广告
在自传和其他回忆文章中,巴拉德多次提及“记忆”。记忆如何存在于思想的深水域,如同海底的沉船。将其拖向日光之下是危险的活动。那段上海记忆有太多不容易用小说处理的东西了。等他在《太阳帝国》的续作《女人慈悲》(The Kindness of Women)1991年出版之际,在45年后回到上海——“我能一眼看到两个上海:比昨天更新的摩天楼都市,以及我儿时骑车穿过街道的老上海。”他曾担忧是否离开太久,这座城市已无法与他的记忆吻合。但后来发现,这些记忆拥有如此惊人的适应力,他仿佛回了家,像是要接上1946年因去往英格兰的阿拉瓦号的启航而中断的生活。
而《太阳帝国》的结尾,吉姆在1946年乘坐阿拉瓦号启航之时——“他的思想只有一部分会离开上海。其余的部分将永远留在那里,就像从南市葬礼码头下水的棺材一样,会随着潮水返回。”
巴拉德在《生活的奇迹》中说,“我时常怀疑,是否日常现实并不存在于(上海)这座城市”。我在去年看到发自作为(“首个大型”)集中隔离区的江湾体育场(在小说的年代是“市立体育场”)的一位母亲的求助微博时也有类似的感想。在我将体育场彻底丢掉多年后,它以如此超现实的方式重回眼前。

江湾体育场,2022年5月(新闻图片)


1935年
因原出版方计划变动,上文所引《太阳帝国》译稿版权已回归译者,若有编辑感兴趣,欢迎后台留言联络。对《撞车》(Crash)译稿感兴趣的编辑,也欢迎联络。
对巴拉德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胡凌云对巴拉德自传《生活的奇迹》的书评《从上海到内层空间》。(从上海到内层空间 | 掘火档案 (digforfir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