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遊2009年(PART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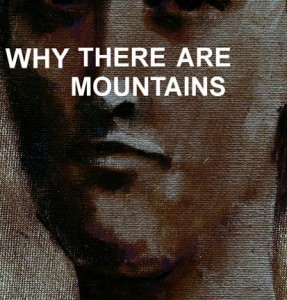
文/肥内
5.电影讨论课
一个年度观影回顾拖了这么久,似乎我也已经感觉疲劳了。读者可能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要将后面未写的部分通通浓缩,或者索性不写也有可能。
对我个人来说,与其说写文章,我经常更喜欢讨论的方式。不过这种讨论需要有一些前提,就是大家是要站在同一个层次上来讨论的。倒不是说对话者对电影有相同的理解,而是说,讨论的内容需要往上提升,以刺激彼此进一步的思维。因为我喜欢人家对我说的东西进行反驳或回馈,让我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论点,进而修正或完善它。
不过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矛盾,好似有些想法还是得在书写时才能落实。应该说,很多论述也是要在书写的过程中,重新沈淀、整理,以有条理地写出来。等于是在书写时,变成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好比说,正在写的论文就是这样,我已经因它跟我自己进行过无数的对话,不管是在脑袋里还是把这些对话写出来。
无论如何,对话总会引发各种不可预期的形式与内容。于是从2006年初,为了在听过黄建宏在台湾的电影资料馆进行的一堂讲座: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论点看《葛楚》(Gertrud,1964,很可能有些朋友还记得我曾贴在台湾的博客以及豆瓣日记中,关于这堂讲座的现场笔记)之后,一些在我煽动下前往听讲的朋友,要求我放映这部片,因为我们都不是电影数据馆会员,所以免费的活动仅能参加讲座,不能观赏影片。于是我便想,既然要为大家放片,那不如把恩师从2003年便停下来的「影书会」给延续吧。
影书会是恩师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弄的一个影片欣赏讨论会。算是延续那个暑假恩师为我跟几位朋友特定设计的一个名叫「我们的电影游戏」的电影课程之延伸。当时来报名的学员里,有一位正在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说她正在写的论文是关于文学改编的。不过这位学员不知怎么回事,电影课程的最后几堂几乎都没有来。尽管如此,恩师还是特定将影书会的最初几堂都安排为文学改编的影片。所以在这仅有的五堂课(每月一次)里,每个月都要讨论一部片跟该片的原著。这些影片依序分别是:《陌生女子的来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1948)、《蝴蝶梦》(Rebecca,1940)、《奥赛罗》(Othello,1952)、《审判》(The Trial,1962)以及《地铁的莎吉》(Zazie dans le Metro,1960),穿插一下八卦,作为我师兄的朋友,当时还没有发片的张悬也曾来参加过半堂影书会,所以跟她也算是有一面(模糊)之缘吧,哈!后来随着「桌上电影」课程的举办,这个影书会就暂时告停。后来因为老师身体状况的问题,它也就没再继续了。不过影书会的形式与其说是讨论,它更多仍是老师给我们灌输许多知识。我呢,怎么也不敢妄想「给人家知识」,所以06年重新办起的影书会,就被我改称为「电影同好会」。我也只能用我仅有的一些电影知识,透过讨论的方式,为参加的朋友做一些解答与交流吧。
不管怎样,厚颜如我,从2006年初到2007年中(截至我到北京学习之前),总共应该办过19次的「电影同好会」。在我感觉,即使有过这么多次的讨论会经验,每一次对我来说都像是第一次一样新鲜。因为我觉得,就算可能在事先就有一些可能的讨论方向(由我来设定的),可是在讨论过程中,非常少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走的。这也是为何我喜欢读一些访谈以及圆桌会议的文章,都是非常有趣的。当然我主持的讨论会跟《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的那种圆桌会谈水平是不可能能比较的。
后来有机会读到台湾网友周星星翻译的一篇巴赞(André Bazin,看来,大师的名字将会从头贯穿通篇回顾文了)名为「怎样介绍跟讨论一部片」的文章,发现巴赞毕竟是我的精神导师,他所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也经常能在他的影评中,看到他始终如一的态度。以下我转贴他在文章中列出来的方法,感谢周兄的翻译:
介绍:
- 一,片名以及影片完成的年份(偶尔加进跟这影片有关的相关条件)。
- 二,导演的名字。这部片在导演的创作生涯中占有什么地位,因此要提到这部片的主要特点(内容跟风格)会是什么……
- 三,这部片在当时的价值是什么──在人文/人性的层面上──以及在电影艺术的层面上。
讨论:
- 一,观众的观感是什么;从这些观感出发,可「追溯」到什么……
- 二,表达出来的想法 (idées) 是什么,这些想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 三,从戏剧的观点来看,价值是什么:这个将之戏剧化的过程,有把那些想法减弱──曲解──真正地达到功用吗?等等。
- 四,它的表达形式,它的价值,它很单纯的各种特点(跟其它的风格作作比较──请参考电影史)。
- 五,把它跟其它的影片作比较,列出要比较的部分,经由书籍、舞台戏剧等等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加完美地把我们正在研究的电影作品置放在某一位置。
巴赞的这篇文章,于2008年,《手册》于每期杂志中都刊登一篇巴赞文章,以纪念他逝世50周年,这篇文章重新被刊载在2008年3月号(632期),显见,巴赞对讨论影片的方法介绍在当今的电影学习上仍有它的重要性,否则也不会被挑出来重刊啰。
只是说,即使这些工作都备妥了,讨论还是很难往自己理想的方向进行,因为这还牵涉到对象的问题。我记得06年下半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也去了某小区大学,为义工们进行过三次的电影欣赏会。三次放映的作品分别是《巴黎假期》(Paris…When It Sizzle,1964)、《天使薇拉卓克》(Vera Drake,2004)以及《霍尔的移动城堡》(ハウルの动く城,2004)。可是…可能是我的方法有问题吧,第一堂课,大家都还不知道我,不晓得会放怎样的影片,我还细心地写影片介绍、得奖记录以及做课程讲义。但没想到,第一次来了三四十人,却很多人认为影片太过乏味,可能我讲得也不好,中途发现蛮多人打瞌睡的(原来,站在前面非常容易发现坐在底下的人的一举一动,以前都以为技巧好的话,老师不会知道自己在打瞌睡,但…我错了,很明显的,且我根本还没有站到讲堂上去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后来,第二堂就只剩下六七个人而已…不过第二次我就一改讨论形式的问题,更多与参加者讨论该片要展示的道德问题。
这次的经验让我知道,对象其实很重要,人多不见得有助于讨论的进行。来到北京之后,我从没想过要再办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以为在电影学院这种氛围中,按理说,应该有很多爱电影的人会自发性地发起此类活动,显然我太天真了。
但眼看着我的学习期限也要到了,于是有了想跟一些来北京后认识的好朋友们来进行这样的活动,于是我向导师询问了借系上教室放片的可能性。导师因为喜欢我的构想,于是它便被发展成一堂课,但却不能说是一个喜悦的开始。总之,这个活动变成了一堂影片讨论课,但,是没有我的朋友参加的课程,以及,我要再说一遍,参加者真的很重要,不在于程度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心态。它成为一堂课,已经失去了叫人充满兴致来的这个原动力。于是原本诉求参与者的积极讨论,后又变成我一个人介绍我的准备心得。
不管怎样,我在四次的讨论后离开了,在这四次的课程里,每周在准备的时候,对我个人来说,还是相当踏实的。虽然我大多需要花去两天的时间。然而我会发现,收集资料、参考过去的人的分析等,都是相当有意思的过程。我准备的东西,基本上,在讨论上不仅绰绰有余,且,真正的讨论也很少有超出这些数据范围的,且更不客气的说,讨论的东西层次还是稍低的。这也就是为何我不愿意继续,因为在进行过三次的课程之后,仍有人要说「大师的电影就是要让人看不懂」这种议论,那么这种课程基本上对他们、对我来说,都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很显然这些人并没有把心带来讨论课上。
在四次的课堂上,我分别选放了《女朋友们》(Le amiche,1955)、《秋刀鱼之味》(秋刀鱼の味,1962)、《秋天的故事》(Conte d’automne,1998)以及《莫瑞尔》(Muriel ou le temps d’un retour,1963)等。像在《女朋友们》的讨论上,会发现若在讨论影片的故事、情节、人物上,或许大家还能参与,甚至还可以光这样一部片联想一些意识型态的问题。不过,当话题慢慢转向形式的处理、结构问题上,甚至还有一点符号意义时,讨论的步调就变得孤独了:没有人要跟上我。这或许还是我在内地观察到的影片分析弱点,大家仍集中讨论内容以及意识型态,一如大陆创作者也经常只能顾及这两点,对于形式的敏感度仍不足。这不能不说是学电影专业的人的悲哀,就是因为即使学了专业,仍只能谈这些相对比较容易被一般人感受到的问题,以致于我们的专业便无法突显出来,才会让各式各样领域的人来侵占、瓜分电影研究的领域。这种趋势看来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改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专业人士也得继续跟大潮流一起做尽量不同但看似相同的竞争,没办法,是我们自己专业人士不争气才造成自己生存不易的条件,怪不了别人。
然而我所疑惑的就在这里,很多分析的工具说都在,为何就不熟读、熟练,以让人家无法轻易打入我们的专业中呢?好比说,奥蒙(Jacques Aumont)那本《当代电影分析》很可能仍是目前最为权威与全面的电影分析方法教材,不要贪多,只要综合里头几个方法,基本上已经很够用了,就像我一样;倘若能完全透析并时常练习,那要成为大师也不是难事,尤其在华人界来说。
事实上,就是许多人都不了解读书看电影的好处。好比说,在谈到取镜的问题时,德勒兹谈到有关于「线」的构图法,他举出了两个关于水平线的例子,一是纽曼(Paul Newman)导演的《绝不妥协》(Sometimes a Great Notion,1972)以及李洛埃(Marvyn Leroy)的《我是越狱犯》(I am the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1932)。这两部片我也都是迟至今年才看,却深深叫我惊讶。后者利用的水平线很像是我们能在一些忍者片看到的那种「水匿法」,在《七龙珠》里头也曾被戏谑地介绍过,在经过《猎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1955)这类影片的改良之后,这种水平线变得更加复杂,不过《猎人之夜》的处理毕竟不尽相同。可是在《绝不妥协》中的那个水平线同样也攸关生死,但却惊人得多,它还包括了时间的绵延,观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随着涨潮,被大木压在水里的那个人,慢慢无法呼吸,而身边的友人(还是亲人,我搞忘了,纽曼亲自演出的)只能徒劳地不断为他进行人工呼吸,直至空气已经完全无法进到他的肺里。
我相信影史上肯定还有很多在水平线的取景上有独特表现的影片,一本书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但大师已经为我们筛选,留下最撼动人的范例,因为大师的书,所以知道要找这些影片、留意这些桥段,不得不说,看书学电影好处多多。
倘若真能找到这样的伙伴一起讨论电影,也会是人生一大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