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感到行動:衝動—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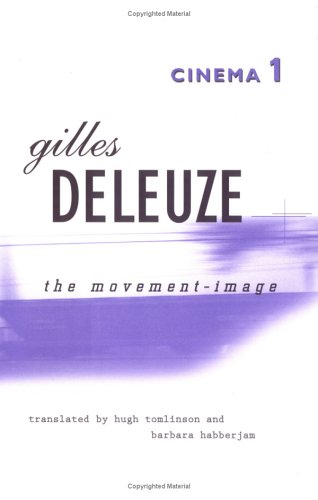
文/于昌民
「…然而在兩者之間,在第一度關係與第二度關係之間,還有些東西看起來像是衰敗的情感或胎狀的行動。」
德勒茲在《電影一》(Cinema 1)第八章談的是整本書當中較為抽象的一個概念,亦即衝動—影像,它位於情感—影像抽象的質性與觀念論與行動—影像決定的情境和寫實主義之間,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如果說《電影一》與《電影二》(Cinema 2)是從電影中的人物出發去談論其在感官動力機制中各種柏格森意義下影像的交融,不管是所有事物事實上都是一種影像,或是主體作為影像與世界作為影像的交流,在衝動—影像當中,此種傾向最為明確。原因在於德勒茲在這章當中談到的一種生發狀態,亦即從情感—影像到行動—影像這中間的間隔事實上是一種混沌的狀態,「(衝動—影像的)原始世界因此也是激進的開端與完全的終末」,德勒茲如是說,而在這其中,浮現的便是電影中的角色,甚至是一種主體狀態,因此,此章所使用的詞彙將聚焦於描寫人物的慾望狀態,亦即,從動情的模糊與獨特性,到語言化的理解並付諸行動之間,某種屬於本能,人物都還是「人—獸」這樣的獨特性格。
也因上述原因,衝動—影像這章分為三個部份:自然主義、布紐爾作品的一個特色、自然主義的困難及羅西。德勒茲不意外地從自然主義開始,因為就他的觀點來看,自然主義就像是尼采口中的「文明的醫生」(physicians of civilization),在這流派當中的作者細心地觀察著人的生活環境,將所有細節都細心的納入寫作當中,像是要耗盡一種環境,在這竭盡當中,原始的世界才從中誕生。因此衝動—影像必然從一種給定的環境當中誕生,它無法脫離周圍環境而自然產生,他是真實人類從情感到行動之間被扯落、被留下的碎片狀態,這些碎片同時也成為影片中那些拜物的細節,如同史卓翰的軍裝、布紐爾的荊棘皇冠…哲學家在這裡給出了兩種對立項:原始世界/衍生情境、衝動/行為模式,就在這樣的自然主義的鐵律下,衝動—影像其不穩定的特質特別被突現出來。在第二個部分則將史卓翰的自然主義和布紐爾的自然主義區分開來,亦即,史卓翰的影像風格跟左拉的更為接近,在給定的環境當中去想像身體的衝動,與動物的本能特性聯繫起來;另一方面,布紐爾的自然主義則朝向「靈魂的自然主義」,因為對於布紐爾來說,這種方式更能夠去精確地描寫變態與衝動本質上其實是人工構建的,甚至可以把這種衝動與信念的超自然宇宙連結起來(也因此他在這章當中提到了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最後一個部分則朝向美國電影當中自然主義的困境,換句話說,如何保持在情感—影像與行動—影像之間,卻又不落入俗套並保持創造力,德勒茲在這裡提出的是雷(Nicholas Ray)的影像風格演進,最後,才進入羅西這位自然主義的最後一位大師。
因此我們有了三位衝動—影像的三位大師:史卓翰(Erich von Stroheim)、布紐爾(Luis Bunuel)、羅西(Joseph Losey)。三位導演都從社會的給定情境出發,將雙重的社會分界(富—窮、主—僕)等描繪出來,賦予其情境底下的暴力與殘忍性,與初始的世界連繫起來,這也是為何布紐爾與史卓翰的作品被巴贊(Andre Bazin)在文集當中稱之為「殘酷的電影」(cinema of cruelty)。而在這偶一浮出到吞噬影響的初始世界當中,時間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在史卓翰的《貪婪》(The Greed, 1925)當中,米特里(Jean Mitry)我們看到了電影史上第一次描寫「心理綿延」(psychological duration)的作品,時間在我們面前並不是展開,而是崩壞,消解自身。箇中緣由來自於衝動—影像處於情感—影像和行動—影像之間,它不再具有情感—影像所堅持的純淨與模糊的獨特性,例如說某種感受到的特異知覺,但它也不是完全付諸於行動那般推動敘事,像是我們所有的模糊知覺成為了衝動,而衝動再成為了行動。衝動—影像之所以帶著一種破敗、衰滅的氣息的原因就是它看起來像是處於行動—影像之後或是之前,那被賦予的人物也許完成了行動,也許還在醞釀,但呈現它所附帶的一種人物的衝動、慾望、本能的狀態卻在此一階段被赤裸裸的展現出來。它既是衰敗的純粹,卻又尚未完全具現成固體的情境,讓它處於一種流質、黏膩的影像狀態。史卓翰在這其中展現的衝動就是一種加速的敗滅,加速的熵,讓已經成型的社會情境與行為模式再度融化成為慾望的泥淖,而他影片中的那些光和影,事實上,就是他將時間視為一種熵,而讓光線從屬於其下(此一熵的定義當然可以追回熱力學當中物質自然往不穩定狀態傾斜的情形,但同時也可以是更接近精神分析式的定義,一種餘熱,在化學作用過程當中自然散發出來的過剩能量,無法被象徵界完全含納的過剩)。因此,這種脫離敘事的爆發與流淌就讓德勒茲說出,「無疑地,自然主義電影的偉大成就就是如此靠近時間影像。」
自然主義的電影作品則可以分為四個層面討論(德勒茲在此從討論衝動—影像將問題轉置到自然主義的電影上,似乎對他來說衝動—影像也許正式偉大的自然主義電影所追求之物),分別是衝動—影像、衝動的對象、以詭計獲取環境提供給他的所有東西,像是在這其中所有東西無差別地可以滿足他的慾望、並存且接續的真實、特殊的情境。前文我們談論的衝動—影像是為何物,到這裡要更複雜地去談論其對象、邏輯策略以及情境。衝動的對象大體上來自於原生世界之物,但它同時又是衍生情境之下被撕碎、留下的碎片,換個方式說,脫離原本的符號的脈絡,他成為既熟悉又陌生的「部份客體」,從此就衍生出了一種可能的拜物主義。在第三個部份上,則是衝動的邏輯:在給定的情境之下,主人翁不是為了達成目標,而是為了他自身的衝動可以選擇這個受害者、但那個受害者也無所謂的一種邏輯;對象為何並不重要,只要對象能夠暫且舒緩主人翁的衝動,那便可以了。最後則是突出的社會情境,如僕人的生活與主人的生活、富人的生活與窮人的生活。史卓翰在這部份則是悄悄地去描繪富人如何浩劫自己的生活情境,慢慢侵入窮人的生活當中以獲取獵物;布紐爾則採取相反的途徑,窮人像是禿鷹或野狼般等待時機,靜候時機成熟,讓衝動突然彰顯在影像之中,將原有的情境擊碎,去攫取碎片,讓影像的調度風格在某個時期像是從垃圾堆中顯現而出。
如果說史卓翰的作品是一往下的斜坡,邁向不停加速的熵,那布紐爾作品的衝動狀態則以重複的方式展現在電影當中,就像《泯滅天使》(The Exterminating Angel, 1962)當中,賓客上樓的片段完全一樣地出現了兩次,更別提《中產階級的拘謹魅力》(The Discreet Charm of Bourgeoisie, 1974)當中對於用餐的執著與中斷。然而,就像前文所題到的那樣,布紐爾的作品雖然是在重複當中凸顯出其最重要的特質,但導演仍然賦予這樣重複的特質救贖的可能,即使他對這樣的可能性有著深深的懷疑,德勒茲認為,這與布紐爾作品當中對於基督教的執著有絕對的關係。
最後,在美國電影當中也依然可以看到衝動—影像的蹤跡,尤其是在雷的作品當中特別突出,我們甚至可以在他的影像風格的演進中去尋找各式各樣的衝動—影像。雷的作品在五零年代時特別關注青少年的問題,尤其是在《養子不教誰之過》(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中特別突出。青少年所處於的位置正好與衝動—影像的情境相類似,從不知如何語言化、符號化情感的孩童位置邁向行動的主體與成人,然而雷的作品就跟富勒(Samuel Fuller)一樣,終究是逃脫不了古典好萊塢主義對於行動—影像的執著,只是在這其中,富勒在B級黑色電影的製作體系發揮的更好、也走得更遠。不過,此一時期仍有一位重要的電影作者從自然主義電影的脈絡浮現而出,英國導演羅西展現衝動的方式擺脫了寫實主義的行動的暴力(violence of action),而是展現了某種靜態的卻正在活躍的暴力(violence in action),並把這種元素凝結在此處,成為他電影中最突出的風格元素之一,《僕人》(The Servant, 1963)很好地說明了此點。而如果說她真正延續了自然主義的什麼的話,那就是給定社會情境中主僕的辯證與對立關係在他的作品當中成為了全然的順服(servility),看看《克萊恩先生》(Mr. Klein, 1976),德隆(Alain Delon)所扮演的主角在電影中被誤認為猶太人,然而,他最後也像是認同了這樣的說法,搭上了往集中營的列車,一去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