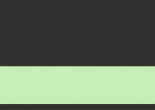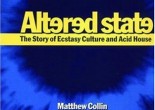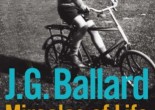书评
日本科幻动漫简史
押井守的《攻壳机动队》有着细密的动画和很高的制作工艺,但角色在视觉上是平面的,特别是和《怪物史瑞克》之类近期电脑制作的电影相比。学者和影迷并不觉得这是日本动画技术的缺点,而认为这种美学是蓄意的,它强调了漫画和动画的联系,是动画吸引人的基础之一。
從情感到行動:衝動—影像
箇中緣由來自於衝動—影像處於情感—影像和行動—影像之間,它不再具有情感—影像所堅持的純淨與模糊的獨特性,例如說某種感受到的特異知覺,但它也不是完全付諸於行動那般推動敘事,像是我們所有的模糊知覺成為了衝動,而衝動再成為了行動。
行囊里还存有碎了的梦想
而王小峰则回头寻找,把埋没于风沙中的里程碑一个个都挖了出来。读这个故事,无须记着主角的真实来头,更不用把它和作者的其他文字联系起来——无论是乐坛巨星或是著名博主,在黑暗之中也只剩下自己。烟头不是灯塔火炬,它只能照亮自己的脸,但它能照亮自己的脸。
关于『音乐使人自由』的「自由」乱谈
redhousepainter:音乐人的自传,无非是看八卦,但八卦也有深浅之分,一看作者肯否赤裸裸,坦荡荡,二看编辑是否穷追猛打。mimida: 书名是「音乐使人自由」,没错,我相信音乐确能使人自由,不过这还都取决于你愿不愿自由,更根本的是你敢不敢自由。
等待酷斯拉
在五十年代,电影Godzilla是对好莱坞恐龙式生物电影的典型西方主义改编。在九十年代后期,在东宝株式会社和美国三星电影公司一份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之后,怪物Godzilla奠定了国际超级英雄的地位。我相信这位超级英雄,作为一个跨文化的、通用的和后东方主义的后现代怪物,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继续娱乐我们。
胡总的书是如何诞生的
除却胡总常用的“您”这类的称呼外(这很是他个人的直接写照,对吗?),读者最先注意到的应该就是内文的设计吧。排成这样并非是随意为之,有两个考虑,第一是胡总曾强调过的“理工男不喜欢多余的空格”,第二是用什么字体来对应这种方案是最佳的。
Far away,so close
早年混迹在胡老师那个简易的小论坛上的时候,印象很深有个姑娘的ID叫“林繁叶静”,其实这是她和自己男朋友的真名,他叫林繁,她叫叶静。这个姑娘一次跟贴里面有句话说,“这么多年了,我和我男朋友的感情一直出奇的好”。当时我觉得她可真没劲,谈个恋爱也不轰轰烈烈的,还一谈这么多年。
讀《電影美學概述》
在我看來,電影理論無疑是電影美學的基礎背景知識,然後再針對各種表現手法的情狀進行探討,尤其問:為何需要這樣?這樣做是必要的嗎?有沒有達到預定的效果呢?以及還有沒有別的方式?會不會更好?這篇筆記主要針對書中的各章進行簡述。
電影:讀書與筆記,091123
「靈光」的消逝很可能只是一種憂鬱的感傷(話說憂鬱若正代表了20世紀的特質,本雅明也不過是順應潮流的感傷罷了,「靈光」的逝去是無須被摘貶),因為現在傳播媒介如此便利,以致於我們根本不會錯過什麼認識藝術品的價值,早在我們懂事之前,《蒙娜麗莎》的地位已經深植我們心中。
观看之于我,就是一种欢愉
今天回了一封信给老师,其实早该写了,但是却迟迟没找到一个话题,直到我翻开了阿拉斯(Daniel Arasse)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1),见着了第一篇文章中的一些看法,使我动笔(动手指打字)写信给老师,并且在几个小时内,也让我不断去思考一个关于观看的问题。
跳舞的政治
音响靠柴油发电机驱动但音量巨大,DJ播放着电台里没有的舞曲。他们的血液中没有一滴酒精,只奔涌着E字开头的药物——那一年,伦敦的青年们迎来了锐舞运动的全面升级。也是在那一年,曼彻斯特的青年们在俱乐部听着乐队起舞,迎来了锐舞超越摇滚的拂晓。他们的T恤上写着:伍德斯托克’69, 曼彻斯特’89。
从上海到内层空间
此书并非一部详尽的传记,略去了很多重要人物,诸如他的儿子和一些新浪潮科幻的代表作家,对自己的生活也略去很多时期很多细节,也缺乏对个人作品的分析解读,这难免让读者失望。但造成这些遗憾的原因,与其说是作者身患癌症心力不足,不如说是他刻意简化,希望读者能读到“奇迹”而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