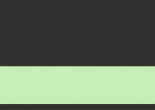影评
弗利兹‧朗:流亡好莱坞的黑色符号
朗所呈现的探索经常又是一种已知,因为一且都是命定,人物的挣扎终究是一次徒劳的过程;朗自己则是迎接一片黑暗,在他息影之后不久,他便失明了。他所厌弃的世界最终被隔绝在黑暗之外,但他所带来的影片不会只是一种苦涩,而是让被判刑的主人公成为体制中最大的反讽,进而达到他的“载道”理念。
千真万确的罪
任何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绝不会因为它具有天真无邪的特质而汇聚众人的目光;往往,这个地方的“罪”便是它的闪光点。罪——罪恶?罪孽?罪过?原罪?基督教的七宗罪借那部著名的电影早已广而告之:嫉妒,贪婪,傲慢,暴怒,懒惰,贪食,色欲。这七种原罪,宿于每个人、每个区域、每个时代;当然,它们也深入好莱坞。
Screening Modernism, Part 1
藉由分析風格史(從巴贊到包德威爾的這條脈絡),發展對於現代電影的概念,並且在藝術史及限定數量的美學/風格特徵中理解這一被歷史決定的整體,並將其連結至哲學或社會環境以生產在歷史語境中的意義。
夏布洛,下好離手!(權充悼文)
夏布洛總是讓自己賭上一把,冒著同儕間最受批評的名號,不斷有意無意地押錯號碼(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慢慢地,他從押單號改押顏色,賠率小但輸的機會也縮小了。下好離手,沒有反悔。
像河边的树一样生活,等待巴比伦的毁灭
虽然此片充满喜感,但因为先前读过太多牙买加社会的动荡和音乐家命运的坎坷,我观看时还是没能大笑。不过,也许正是乱世促成了伟大的艺术,而穷人买不起房子,就只能全身心拥抱文化。借用人们对reggae音乐的描述,片中从容的幽默感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主义的乐观主义”。
讀《電影美學概述》
在我看來,電影理論無疑是電影美學的基礎背景知識,然後再針對各種表現手法的情狀進行探討,尤其問:為何需要這樣?這樣做是必要的嗎?有沒有達到預定的效果呢?以及還有沒有別的方式?會不會更好?這篇筆記主要針對書中的各章進行簡述。
試著粗略地整理一下對《全面啟動》(inception,《盜夢空間》)的一些思考
這種囉唆就像我曾評述過《頂尖對決》時說過的那樣,只會遏止觀眾「重看」的興致。只是,諾蘭的進化至少還在於將各種商業元素進行稍微複雜的整合,只是他目前的程度僅能如此,我們又夫复何求?
「幻影」的透視影像作為生活的開展:從《去年在馬倫巴》到《幻之光》
在此我們可以發覺線性透視法作為一種古代的「寫實主義」與攝影影像作為一種現代以至當代的寫實主義時,兩者結合時所出現的並不是更加寫實的影像,而是有其他東西產生
世纪末的女神们
Motoko、Rei和Lain无数次反问自己的话就是:我是谁?由于Cyberpunk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密切渊源,因此她们并不是古典时代被供奉起来的神,而是人类用来实现某些秘密计划的终极工具,一种工具化的神。
一堂德勒茲上課筆記:屬人、屬物係統的交替
當我們注視著它,它也以一種持續、穩定與被凝視,甚至「反射」而反過來注視我們,它現在成為主體,觀看主體,不再是一個面孔,而是為被看者的我們的「強化映射」,因而它「解面孔」(dévisage) 。
透視法作為一種形體形式
在此,我們將把透視法看作形體力量展現的形式。如果說電影影像是一種想像的匯聚和形象的遷移,同時是一種歷史凝聚與美學移轉的表徵,透視法在現代電影中的造形性特色就非常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