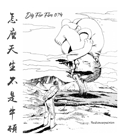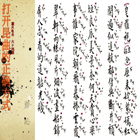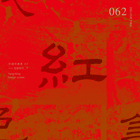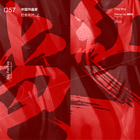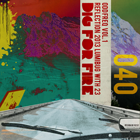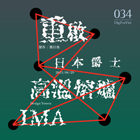撰寫〈電影中的貝多芬弦樂四重奏〉一文的筆記
對於是否發這些筆記,我猶豫再三,最後還是發了,也算是提供某些影片的參考資料,比如對勾搭(Godard)的《芳名卡門》或岡斯的《貝多芬傳》。
02/21 0个评论
《心理地理》2018新版前言|连载
当公共空间的监控越来越多,徒步运动越来越被限制,行走者,游荡者,漫游者,是否还能在其中找到空间进行活动?在这样的城市,有着不可阻挡的离心逻辑的经济力量正在排空中心,将居民们前所未有的向外重置,想成为心理地理人的他们,能留得起吗?
02/10 0个评论
掘火中译 古尔达:那又怎样?!
他用爵士的玩意随意玩弄我的肖邦,当时的感觉就像看到一个猿人伸出毛手搭上了蒙娜丽莎的肩膀,细眯的眼皮里猥亵的欲望可见一斑,所以这就是我对古尔达的第一印象
02/08 0个评论
筆記《魯貝的光》
寫到後面基本累了,筆記就寫得少了,且慢慢有些想法浮現,想寫在影評中,所以也就沒有顯示在筆記中;當然,最後寫作的過程又是完全不可控,因此,那些「想法」大概很少留到正式文章
02/03 0个评论
掘火中译:伯恩斯坦《年轻人的音乐会》| 两只芭蕾鸟
拉威尔很喜欢《火鸟》,但是更喜欢《彼得鲁什卡》或《春之祭》……巴黎的观众渴望欣赏先锋派艺术的邪味,按照拉威尔的说法,《火鸟》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对于他的解释,我还要补充一句:《火鸟》符合它的时代风格。
01/25 0个评论
一枚分析与自我分析案例
一种系统化的,安排得当的文化生活与漫无目的的消遣取乐分道扬镳,也因此,那种自觉自律的生活无需依靠外来的指南,它由始至终被一种内生的秩序规定着文化行为,这大概就是让我彻底绝缘于微博、豆瓣等文化社交平台的重要原因。
01/17 0个评论
2019现场二次体验
想象太阳底下的另一个世界里,马勒拿一罐子可乐,坐在沙滩椅子上,看着湖景晒太阳。或是望见有个游客过来,拄着登山杖站起身,走到游客跟前想拉着聊天,说到激动处,还跺脚,敲登山杖。
01/10 0个评论
掘火中译:伯恩斯坦《年轻人的音乐会》| 肖斯塔科维奇生日致敬
而以上的这些反类型反套路的设计,这些虚晃一枪的情节走向,欺骗式的镜头剪辑,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九交响曲》里面全部都有。感到很奇怪吗?
12/28 0个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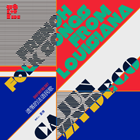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https://www.digforfire.net/wp-content/gallery/radio-140x140/086-140x14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