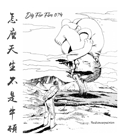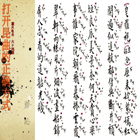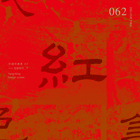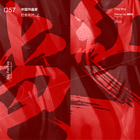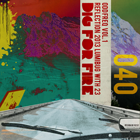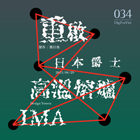利马的非洲裔秘鲁音乐(一)
了解这层非洲裔秘鲁人与西班牙语文化的关系,能帮助我们理清非洲裔秘鲁音乐的历史脉络。因为,17、18世纪以来形成的criollo音乐,正是非洲裔秘鲁音乐的原型。
观看的欢愉与其他——于昌民电影讲座
藉由閱讀電影,如同馬希(Michel Marie)所說,「延長觀影的愉悅」,同時也可能理解到,電影不僅僅提供歡愉,電影也提供了一些其他的東西,使我們更瞭解自身。
《與安東尼奧尼一起的日子》:一部電影兩場戲以及兩個靈魂的交會
如果這本日記沒能符合讀者對揭開影片的創作核心,以及導演的思索過程的要求,那麼最起碼,它揭示了兩個電影工作者的真誠,同時也喚起了讀者對這部影片的好奇,而好好地觀賞這部影片肯定是兩位導演一切努力的最終願望。
末世新声(二)Whole Lotta Shakin’ Goin’ On
当我们称摇滚乐为一种音乐风格时,这是指我们正在说的这些,而不是指一种陈腐或苍白的模仿(虽然已经有了不少此类玩意儿),它是一种鲜亮的光芒,一种探索和冒险的态度——一种前途无量的音乐。
想飞 ——从无情节意义的电影结尾看导演处理
导演的功课在于,用实在的影像去表现一种最虚幻的情怀。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导演需要做出决定,对戏的虚实做出界定。这是电影创作中最难把握的一环,也是电影能让人激动之所在。
归零地:进步与毁灭
袭击发动者的匿名性,对所有人而言,仅仅标志了一种全球的隐秘状况,一种在“善恶的彼岸”的私人犯罪之未知量的降临,数个世纪以来,“善恶的彼岸”还一直是一种偶像破坏式进步的高级牧师的梦想。
西柚 Rothko S.L.A.
这些“指示”也被称为“Event Score”。另一个关键词是“Fluxus”。Event Score 由美国概念艺术家和先锋作曲家 George Brecht 所发明,之后又被La Monte Young和野奶奶等发扬光大。Event Score背后的幽灵是约翰笼子。笼子曾在58-59年间为Brecht传道授业解惑过,解惑地是纽约的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跌落于恐惑谷(Uncanny Valley)的充气娃娃及其他
其实,支撑恐惑谷现象的是一类“通用型”(而非特异性的)心理机制,不只是仿真机器人这类具有拟人态的认知对象才能引发,主流文化及主流人群之外的认知对象常有引发恐惑感的能力。
查特贝克,他的生平和音乐(第三章)
查特从来不怕演奏时出错,他的小号总是随心所欲,表达着自己的感觉。Mulligan的演奏往往弥漫着浓浓的学院风味——听众可以听到他小心地变调——而查特那精彩的独奏则源自自己无数次的思索,试验,还有对即兴音乐敏锐的洞察与感受力。
我犯過很多錯
他認為「人類不可溝通性是永恆的」,山謬爾則補充說或許是「利己主義」,導演馬上接著說,他曾想過自《擦鞋童》以後的影片都能冠上這個詞:「利己主義1號、2號、3號,那麼《風燭淚》就是『利己主義4號』」。
侯麥的死亡一躍(salto mortale)
他不停的讓角色在故事中不顧一切,做出信仰的跳躍,像是一切並非為選擇什麼,而更執著於選擇行為上。侯麥這一跳,就躍離我們去了遠方,眺望檢驗著他帕斯卡(Blaise Pascal)式的賭注。
来自那个时刻的记忆与感触——Echospace访谈
当我聆听我创造的音乐时,我脑海中出现的是某个时刻,来自那个时刻的记忆与感触。我的音乐一般来说是一种对我周边世界的反映,包括我的家庭、孩子、还有与Techno和城市无关的孤立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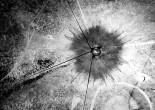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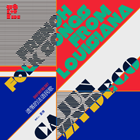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https://www.digforfire.net/wp-content/gallery/radio-140x140/086-140x14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