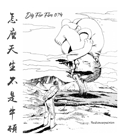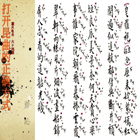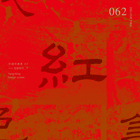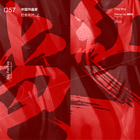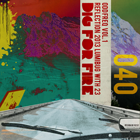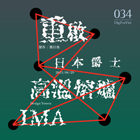周遊2009年(PART III)
猪怕肥,但人不怕成名。用「肥内」这个名字在网络上也闯荡了逾六年了,今年总算有媒体主动邀我去看影展了。不过影展呢,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近情情怯啦。2009台北电影节依旧乏善可陈,大概是我想看的影片,多数都会自己买碟,新鲜感相对低一些。
周遊2009年(PART II)
安东尼奥尼这部电视片,或者说「录像片」,有一处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两三个空景中,多是拍摄草地,他透过调光装置(不确定是附在摄影机上的还是后期调整的)让色彩的变化,直接保留在画面上。他透过这个调色的过程,是想向观众传达什么吗?
2009年周游——我的年度观影回顾
这次再写,或许也是因为算是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结束做个纪念吧。而这个十年也刚好是我开始学电影的十年,对我个人来说,无疑也是意义重大的。以下的周游,就是今年看的影片所带我畅游的,有时间且有兴趣与我同游的朋友,就请您花点时间一起来吧。
Life on Planet Groove Vol.2
Jon Hassell and Blue Screen Marvin Gaye 24 Carat Black Black Ice Tom Brock Vibrations 巴西贫民窟 Roy Ayers Herbie Hancock
昨天晚上我梦见……Morrissey的演唱会
从剧场旁边的地铁站里一出来,马上就感受到了铁杆乐迷们的热情,音乐会是看观看陌生人的好地方,这里的观众大部分稍微有点儿书呆子气,打扮得很认真,剧场门口的人群里,偶尔还冒着着英国/苏格兰口音。和这间富丽堂皇的Art Deco剧场也算相映成趣。
文艺女青年的最佳night out
比邻各色背景的劳动人民居住的East End,靠着东伦敦的港埠,这个上世纪初很多中国水手集结的地方,我们可以从经常出现的以‘传道’为名的楼房体会到他艰辛沧桑的历史感,虽然现在沾着不远处的经济中心Canary Wharf和West India Quay新起的高级公寓的光,Limehouse还是没有摆脱那几分暗里做事见不得人的感觉。Troxy这个20年代的art-deco风格的前电影院,加上内部带着80年代俗艳色彩的装饰,或更适于做一个东伦敦黑帮控制下的舞厅,却成为了一个不错的有点突兀的摇滚场所。
Last Night A DJ Broke My Heart
听着某些人叫唤他为教父、神blabla的,真不是滋味,糖蒜电台采访去看/参与演出的DJ观众这期节目一开头的哈巴狗气味让我难受。
Frieze Art Fair——全球当代艺术的温度计
尽管Frieze的定位属于非营利组织,但是很明显,通过这个平台来兜售自己的作品是个黄金级别的渠道。据称,在2006、2007这两个当代艺术极其火热的年份里,只要是进入Frieze的作品必然等不到展期结束就被抢购一空。这也彰示了Frieze不仅在商业上成绩显赫,并且也是当代艺术市场起落、作品价值定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電影:讀書與筆記,091123
「靈光」的消逝很可能只是一種憂鬱的感傷(話說憂鬱若正代表了20世紀的特質,本雅明也不過是順應潮流的感傷罷了,「靈光」的逝去是無須被摘貶),因為現在傳播媒介如此便利,以致於我們根本不會錯過什麼認識藝術品的價值,早在我們懂事之前,《蒙娜麗莎》的地位已經深植我們心中。
我是激b我怕谁
但那天永生难忘,毕竟是我们崇拜的长者,毕竟在cpu过热n次之后,大师还是不屈不挠,屡屡用音乐还击,没有抱怨,没有情绪,只有认真解决问题的行动,尽量让演出完整结束,并encore了一曲。这才是把音乐当作工作的精神,我太感动了。
有魔才有佛——专访秋天的虫子
编者:在十年前的夏天认识了秋天的虫子。上地的地下排练室,西三旗三居室里满屋子油画、乱窜的猫狗和乐手,构成了我对北京最后一些鲜明的回忆。十年间只见过他们一次,住在与艺术家无关的无名小区里,有了新的兴趣和信仰,安详着发胖。
观看之于我,就是一种欢愉
今天回了一封信给老师,其实早该写了,但是却迟迟没找到一个话题,直到我翻开了阿拉斯(Daniel Arasse)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1),见着了第一篇文章中的一些看法,使我动笔(动手指打字)写信给老师,并且在几个小时内,也让我不断去思考一个关于观看的问题。
Life on Planet Groove Vol.1
【life on planet groove】无在乎广度,深度,我以为光水平线上和地上的风景就足够耐看。如今(已经不少年了)流行潜入海底两万里,或者学孙悟空跳个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可说句挺丧气的大实话:音乐,听来听去,无非就是那几个人罢了。
跳舞的政治
音响靠柴油发电机驱动但音量巨大,DJ播放着电台里没有的舞曲。他们的血液中没有一滴酒精,只奔涌着E字开头的药物——那一年,伦敦的青年们迎来了锐舞运动的全面升级。也是在那一年,曼彻斯特的青年们在俱乐部听着乐队起舞,迎来了锐舞超越摇滚的拂晓。他们的T恤上写着:伍德斯托克’69, 曼彻斯特’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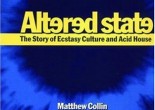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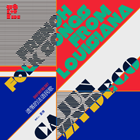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https://www.digforfire.net/wp-content/gallery/radio-140x140/086-140x140.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