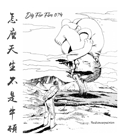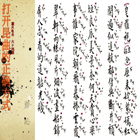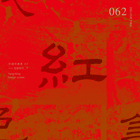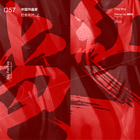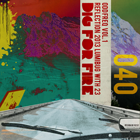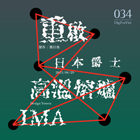小津集成02:1927~1928
一場在酒吧的戲,我們用了很多小號的燈光設備,在每一個鏡頭都要挪動它們。因此,在拍了幾個鏡頭之後,地板就佈滿了電線。既然拍攝前都要花上很多時間跟力氣去整它們,我便把攝影機往上調,以避免拍到地板。我喜歡這種構圖,同時也可以省下時間。
小津集成01:代序:《小津的反電影》導言
不消說,最終在小津影片中是沒有「小津式」的東西,這些作品處在一個意義會不斷地從特定稱謂中,拔錨浮動的世界。也就是說,讀者在聽到小津先生的電影被以這種反覆、無意義的方式描述,將不會感到奇怪。確實,通過熱情地稱它們為「小津式」,我們欣賞他影像的玩味與深刻,我們享受觀賞他影片。
從《土耳其人的聖母》論現代主義電影中的身體
他成為了德勒茲在《千高原》所論的無器官身體,無法定型,無法被認同,它所經歷的儀式只是將身體形象不停地轉換,最終面對其自身的耗竭,如同他在《隱士居》裡所說的:「對於那些愛我的人來說,一切都結束了。」
Ambient Music计划(序,第一辑)
作为体系不在此处、现代音乐根基弱、意识技术老套、旋律感缺失的本国创作者来说,这也可作为并一直作为一个捷径存在,它所重的根本是一种虚无的无标准的东西,又或者可以称之为“XX”或者“XX”。
关于『音乐使人自由』的「自由」乱谈
redhousepainter:音乐人的自传,无非是看八卦,但八卦也有深浅之分,一看作者肯否赤裸裸,坦荡荡,二看编辑是否穷追猛打。mimida: 书名是「音乐使人自由」,没错,我相信音乐确能使人自由,不过这还都取决于你愿不愿自由,更根本的是你敢不敢自由。
等待酷斯拉
在五十年代,电影Godzilla是对好莱坞恐龙式生物电影的典型西方主义改编。在九十年代后期,在东宝株式会社和美国三星电影公司一份数百万美元的交易之后,怪物Godzilla奠定了国际超级英雄的地位。我相信这位超级英雄,作为一个跨文化的、通用的和后东方主义的后现代怪物,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继续娱乐我们。
晃晃悠悠十二天
拥挤的房间,密集的作为,缺失的网线端口,有限的插排空位,诸如“每人限坐30分钟”各种奇怪的限定令人抓狂。更囧的是高达30%以上的国外记者居然并非用十指敲字输入,而是用两个食指高速的“二龙戏珠”。除了令人挠头的“-30 MIN MAXIMUM”,还有特别订制的水杯。
“民谣救护车”【家】吧站现场录音
2010年12月19日,一辆“民谣救护车”由一些音乐人从北京和广州驶出。随之而来的这股民谣暖流开始在各个城市流动,遍布大江南北。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民谣音乐人,好朋友佟妍而举行的,她得了急性白血病,需要立刻进行第一期化疗。
弗利兹‧朗:流亡好莱坞的黑色符号
朗所呈现的探索经常又是一种已知,因为一且都是命定,人物的挣扎终究是一次徒劳的过程;朗自己则是迎接一片黑暗,在他息影之后不久,他便失明了。他所厌弃的世界最终被隔绝在黑暗之外,但他所带来的影片不会只是一种苦涩,而是让被判刑的主人公成为体制中最大的反讽,进而达到他的“载道”理念。
High Tech Soul —— 浅析plastikman live 2010
回头看看他这几年做的事,似乎他对技术热情大过了对音乐本身的热情:Final Scratch,Beatport,Twitter DJ,如果抛开作为乐迷的偏执,这些事对电子音乐界的产生的影响不亚于10张plastikman唱片。
千真万确的罪
任何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绝不会因为它具有天真无邪的特质而汇聚众人的目光;往往,这个地方的“罪”便是它的闪光点。罪——罪恶?罪孽?罪过?原罪?基督教的七宗罪借那部著名的电影早已广而告之:嫉妒,贪婪,傲慢,暴怒,懒惰,贪食,色欲。这七种原罪,宿于每个人、每个区域、每个时代;当然,它们也深入好莱坞。
胡总的书是如何诞生的
除却胡总常用的“您”这类的称呼外(这很是他个人的直接写照,对吗?),读者最先注意到的应该就是内文的设计吧。排成这样并非是随意为之,有两个考虑,第一是胡总曾强调过的“理工男不喜欢多余的空格”,第二是用什么字体来对应这种方案是最佳的。
写给毫无创意的未来
“理想算个屁啊,爱情算什么东西……自我算个屁啊,信仰算什么东西……我们在纷乱的街道上失声歌唱,唱着那美丽而不如人意的生命,自由算个屁啊,永恒算什么东西”,这是汪峰的《觉醒》里唱的;这也是我们少年时曾经向往过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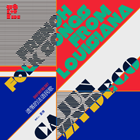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 掘火电台086 :[欧洲自由爵士]之1970年的震颤](https://www.digforfire.net/wp-content/gallery/radio-140x140/086-140x140.png)